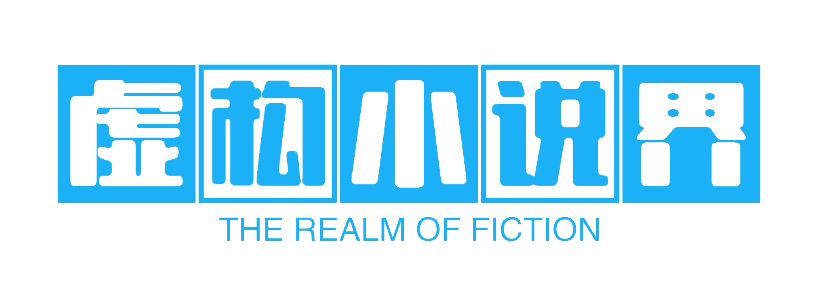第七章
第七章
蘇毓甩手以後,父子倆的日子相比之前就窘迫了許多。
衣裳自己親手洗,方知村口的河水冰涼刺骨。不過徐宴倒是沒什麼怨言。在很早以前,他便跟毓丫提過不必總将他當主子供着,他們是一家人。但毓丫沒聽進去,打心底覺得自己低人一等。徐宴說過兩次見毓丫不聽以後,他便聽之任之了。
如今毓丫醒悟,徐宴雖有些苦惱日常瑣事,心中卻沒太多的不滿。
搓着凍得紅腫的手指,哈了口氣,他仰頭看了眼天兒。天空灰蒙蒙的,安靜得有些悶。
徐宴将衣裳裝進木盆,正準備回去。河堤上突然走過來一行人。
為首的是個三十歲上下的中年男子,國字臉,一身藏青的絲綢長袍,帶着兔毛的帽子,頭發胡子整理得十分體面。打眼一看,通體的氣度就跟王家莊的村民不同。後頭立着三兩個像是下等仆役的青年漢子,弓着腰候在後頭,不過瞧着穿的衣裳料子也十分厚實。下人都如此體面,想必家中非富即貴。
幾個人見徐宴樣貌驚人,粗布麻衣也難掩卓爾不群的氣度,走上前便将他攔住了。
“這位公子,”為首的中年男子臉上藏不住驚豔,說話也十分客氣。隻見他從身後人手中接過一張卷軸,當着徐宴的面小心翼翼地展開,“不知公子可曾見過這畫上的人?”
徐宴比他至少高一個頭加半個脖子,站在近前,頗顯得居高臨下。他鴉羽似的眼睫顫了顫,禮節性地往後退一步。
中年人面上笑容更真切,徐宴靜靜地聽他說完,他垂眸瞥了一眼那畫像。
這畫看起來有些年頭了,紙頁泛黃,畫也有些褪色。不過還算保存不錯,宣紙上一個梳着雙丫髻的鵝蛋臉小姑娘躍然紙上,正歪着腦袋沖人笑。
瞧着神态,年紀約莫在八九歲的樣子。藕荷色的小襖子,脖子上挂了一個金鎖墜子,養得胖嘟嘟的,玉雪可愛。一雙眼睛似桃花眼又似杏眼,作畫之人畫得不清晰,倒是将小姑娘那副活潑的情态畫得紅靈活現。
見徐宴不說話,那中年人又道:“是這樣的公子,這畫上的是我東家十四年前走失的姑娘。這不,東家家中的老泰山重病不起,眼瞧着就沒幾年活頭。臨走前想再見小主子一面。這畫像是十多年前的,如今也不知姑娘生得何種模樣,我等就是想問一下,不知這莊子上可有外地來的孩子?”
徐宴心一動,“十四年前走失的?”
“……這到也不一定。”說到這,中年男子臉上閃過一絲晦暗。不過擡眸間又掩蓋下,“是家中下人發現姑娘不見,據奶娘口述推斷是十四年前,也有可能更早。”
似乎是不願多談,他一言帶過。
轉頭,便又笑起來:“我等一路打聽,估摸着東家的姑娘就在襄陽縣這一片。襄陽縣這麼大,大小村子二十來個。找一個小姑娘不亞于大海撈針,實在困難。不過我聽說王家莊十四年前來了不少差不多年紀的姑娘,不知可有畫像上的?”
十幾年前,王家莊确實從外面買了不少姑娘回來。不過那時候徐宴年紀也小,才三歲,整天被徐氏夫婦關在屋裡,他哪裡會記得?
他淡聲道:“十四年前的話,王家莊至少有四個外面來的姑娘。我家中便有一個。”
中年人一愣,當下便要徐宴帶他去瞧一瞧。
徐宴覺得不大可能是毓丫,他又往那畫像上看了一眼。一團孩子氣也看不出什麼,就這雙眼睛就有點模糊不清。于是也不怕多話地問了一句:“這畫像上,姑娘的眼睛形狀瞧着挺特别。”
中年人一聽,立即就打開了話匣子:“可不是特别?聽說東家的姑娘天生一雙大眼睛。”不過他也沒多問,淡淡一句‘跟我來’,便抱着盆往徐家來。
一行人來到徐家,蘇毓正端了個木盆,坐在小馬紮上在往腦袋上糊藥膏。
這藥膏是她剛搗出來的,她特有的養發護發的方子。蘇毓是無法忍受自己頂着一頭稀疏枯黃的頭發,不管是天生還是營養不夠,她總得讓頭發烏黑起來。這不,一擡頭,就看到徐宴抽着嘴角立在籬笆外。徐宴的身後,四五個漢子一臉不知如何是好的神情,驚悚地看着她。
哦,忘了說,她不僅糊了頭發,還往臉上糊了一層綠綠黑黑的藥渣。
那雙腫得像蘿蔔的手指抓在頭發上,襯着臃腫的身材。不用多想,此時她的情态從外人看來是要多邋遢有多邋遢。
中年人有些被吓到:“公子,這位……”
“是内人,”徐宴有些尴尬,但也坦然地對幾人道,“内人十三年前來的王家莊。”
中年男子湊在一旁盯着蘇毓看了許久,搖了搖頭。
徐宴也沒說什麼,本來就是随口一問。毓丫是與不是,與他來說并不會有太大的波瀾。他将剩下的幾個十三四年前來王家莊的姑娘的人家告訴中年人,得了聲謝,順便給指了路。
蘇毓蹲在院子裡,也不知他們在外頭說什麼。她正撅着屁股努力保持平衡,生怕自己一不小心蹶木盆裡去。透過頭發縫看徐宴跟那人說話,蘇毓發現這藥膏賊難糊。糊半天那點頭發纏纏綿綿地黏在一起,又惡心又髒。但是沒辦法,為了美麗,她就都可以。
天塌下來都阻擋不了她護發!蘇毓低下頭,十分倔強地往腦袋上糊藥膏。
送走了尋人的一行人,徐宴推門進來。
看天快下雪了。這會兒晾也不好,他将盆往屋裡端。
父親在的時候,徐乘風出奇的乖巧。說來這孩子的皮相是真的生得好,估計随了父親。小小一隻蹲在雪地裡,人比雪還白。頭發烏黑如墨鍛,小嘴兒紅似櫻桃,粗布襖子也藏不住的漂亮。他此時蹲在蘇毓的身邊,蹙着眉頭看蘇毓将那一團一團的糊糊抹在頭上。
“你在幹什麼?”小孩兒很倔強,至今不願喊蘇毓娘。
蘇毓:“洗頭。”
“這東西能洗頭嗎?”徐乘風眉心擰得打結,他縮着手往後退幾步,生怕濺到身上,“越洗越髒。”
蘇毓又想翻白眼了。這小屁孩兒就不能張口,一張口,她就想打死他。
剛想讓他走開,徐宴搓着手就從屋裡出來。
蘇毓擡了下頭,從發縫裡就看到了徐宴的一雙手。不得不說,這人是真的長得太不合理了。這一雙手,雖有些紅,但仿佛白玉雕成一般完美。手指細長,指甲飽滿透着粉。骨節修長且骨質均勻,幹淨白皙,沒有一點瑕疵。
這般虛虛地攏在一起,莫名有種欲到骨子裡的感覺。蘇毓看着,眼睛都忘了移開。
徐宴不知她在看自己的手,搓了搓僵硬的手指便放下來:“這是又在做什麼?”
“……”父子倆問了一樣的問題。
蘇毓沒興趣回答,問起了其他:“外頭剛才來的人是誰?”
徐宴自小到大這性子頗有些内斂,一般情況下,遇着事兒,隻要不問,他甚少與旁人說。往日在徐家,毓丫是個鋸嘴葫蘆,輕易不開口。徐宴也就養成了除非事關毓丫,否則萬事不與毓丫說的習慣。不過這會兒蘇毓問起了,徐宴楞了一下,便也張口說了。
蘇毓有些唏噓,沒想到古代也有失孤家庭千裡尋親的:“昨日我去鎮上也遇到了。聽說家中長輩重病,就等着見這孩子最後一面。沒想到兜兜轉轉,居然找到這裡來。”
徐宴對旁人的事沒做評論,點點頭:“總得費些功夫的。”
感歎完别人的事兒,蘇毓斜眼看他。
見徐宴似乎是沒事兒了,她這見不得徐宴歇着的心又跳動了起來。
于是她岔開腿,屁股挨着小馬紮直起腰,張口就理直氣壯地指使他去幹點兒别的活兒:“我昨兒買的那個豬骨頭,還有那些下水。你若是無事,可幫着洗一洗。”這眼瞧着就到飯點了。
豬骨頭炖湯,至少得一個時辰才鮮。那些下水清洗麻煩,也頗耗時辰。不指望徐宴做菜,蘇毓覺得,他洗一下東西倒是可以的。
其實也不是不指望,而是能力所限。徐宴目前的水平,也就止步于燒熱水和煮熟稀飯吧。她雖然想偷懶,但也受不了一天三餐吃稀飯。
徐宴眼皮一跳,垂眸看着蘇毓。
蘇毓挑眉:“不能洗?”
……這倒也不是。正巧這幾日徐宴打算歇一歇,确實是閑着。
蹲下身盯着蘇毓腦門看了一會兒,眼睜睜看蘇毓腦袋上糊糊從頭發滑到臉上,整張臉面目全非。徐宴沒忍住嘴角抽搐,掩着嘴輕輕笑了一下,轉頭便去了。
蘇毓:“??”笑屁?
徐宴的背影消失在竈房門裡,蘇毓哼了一聲仰頭靠着門檻,面無表情地等面膜幹。
昨日那些下水,蘇毓早做過處理。此時隻需再仔細搓洗便能直接下鍋。蘇毓已經很久沒吃葷腥了,這會兒滿腦子鹵大腸,爆炒豬腸。
而竈房裡,徐宴在看到這盆沒人吃的下水和豬骨頭後,整個人陷入了深深的自我懷疑之中。沒養過家,徐宴拿捏不準市面上柴米油鹽的價格。但他還是清楚,這年頭還沒人吃過大腸的。豬大腸裡頭都是穢物,再貧苦的人家都沒吃這種東西的。
徐家到底苦到什麼地步,毓丫會買這種腌臜東西回來吃?
餘光瞥見人影進來,他蓦地擡頭。這一擡眸,就瞧見蘇毓頂着一腦袋的藥糊和一張大綠的臉進來。
若忽略蘇毓的脖子以上,徐宴自然看到蘇毓一身打滿補丁的破襖子。往日徐宴的目光幾乎不會落到毓丫身上來的,不看,所以不曾注意過。此時睜眼看人了,他方注意到,蘇毓穿的衣裳有多破。褲腿上爛出來一個一個的洞。這些破爛,毓丫用黑藍的碎布片縫着,雖然不髒,卻要多寒酸有多寒酸。
昨夜蘇毓哭訴的話在耳邊回響,此時看來并不摻假,徐宴心裡有些不是滋味。
蘇毓身上穿的,比街頭的乞丐身上穿的,确實沒好多少。真要比的話,也就多了一份幹淨整潔罷了。
抿了抿嘴角,徐宴更沉默了。
因為要敷面膜怕弄髒,故意找了箱籠裡最破爛的衣裳穿的蘇毓不明所以。眯着眼睛,摸瞎似的摸到徐宴身邊蹲下。隻見他撸高了袖子,大冬天的那雙漂亮的手和小臂都泡在水中。白皙的手背粉紅姑且不說,手指手掌連着手腕的那一處凍得通紅。
他蹲在木盆邊上,鴉羽似的眼睫覆蓋着整個眼睑,沉默不語。那張清隽的臉低垂着,從蘇毓的角度隻看到他眉心擰出一個疙瘩。
“洗好了沒?”
一聲驚醒了徐宴。
“……這是中午要吃的?”許久,徐宴略帶沉重的口吻開口問。
“嗯,”蘇毓糊得就剩兩眼睛露在外面,沒領會他的沉默,很自然地點頭:“我昨夜已經清理過一遍,你用鹽和面粉多搓洗兩遍便可。”
徐宴:“……這是腸子。”
“昂?”廢話,她買的她能不認得這是腸子?“我會做鹵大腸。”
徐宴:“……”
徐乘風不知何時也湊過來,蹲在他父親的旁邊。皺眉的表情,跟他爹一脈相承:“可這是腸子啊!”
“腸子怎麼了?雞腸你不是也吃了?”蘇毓眼皮一翻,無意識嘲諷,“怎麼?雞比豬高貴?”
徐宴:“……”
徐乘風鼓起了臉,抓他爹胳膊搖晃起來:“爹!”
然而他爹也拿蘇毓沒辦法。
……不管怎樣,在蘇毓的堅持下。十指不沾陽春水的徐宴忍着惡心把這些豬下水全清理幹淨。若不是蘇毓連聲說可以了可以了,他估計要十遍二十遍地搓洗下去。
總體來說,清理得十分幹淨,蘇毓滿意到認可了徐宴作為洗菜的人出現在竈房。
蘇毓是十分會吃的。會吃的另一個意思,她也十分擅長做菜。出國留學那幾年,她為了生存和滿足自己的口腹之欲,鍛造了一手好廚藝。因個人口味,她尤其擅長川菜和鹵菜。所以等她将爆炒的大腸端上桌,香味動搖了父子倆的想法。
抱着試探的心态嘗了一筷子後,徐宴徐乘風父子安靜如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