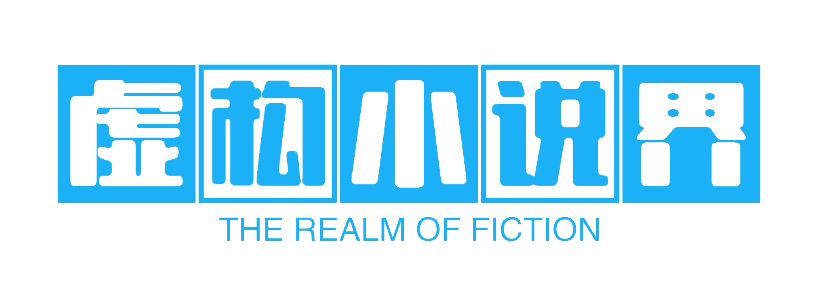第六章
第六章
徐乘風自能說話起,便是徐宴親自帶在身邊教導。這幾年,徐宴聽到的别人說徐乘風都是誇贊聲。
他雖常常自謙,卻也一直以自己教出一個聰穎知禮的兒子自傲。這還是頭一回聽到旁人如此辛辣的指責徐乘風,而這個人還是兒子的親生母親。提及此,徐宴不由臉上火辣辣的。有些難堪。
他臉沉下來,拉着徐乘風便去了書房。
不一會兒書房那邊傳來小孩兒認錯的聲音。蘇毓就沒管,端着藥一飲而盡。這藥一下肚,雖然苦,但一股熱氣就湧上來。蘇毓含了塊糖在嘴裡,轉頭給自己做晚飯。
竈台的火還是着的,她将藏起來的幾個野雞蛋拿出來。煮了飯,又抓了把小蔥,炒一盤小蔥蛋。
菜端上桌的時候,徐乘風正站在門邊兒哭呢。他一雙紅彤彤的大眼睛瞪着蘇毓。不知徐宴是怎麼教的,這會兒到是沒再大呼小叫地對蘇毓不敬了。
他站在門邊兒,徐宴不知在做什麼,人還在書房沒出來。他在門邊站了會兒,又進來。小孩兒年紀小忘性大。沒一會兒就不哭了,繞到桌邊看着蘇毓。人還沒桌腿高,眼睛卻很利,一眼看到桌上擺着好吃的。于是也不說話,鼓着腮幫子委屈巴巴地盯着。
徐乘風:“我肚子餓了!”
蘇毓不搭腔,當沒看見,慢條斯理地吃自己的飯。
徐乘風眼巴巴地等了一會兒,見蘇毓不搭理他,他腦袋一扭,蹬蹬地跑出去。
蘇毓看了一眼,沒聽到開院門的聲音,就沒管。
老實說,雖然剛才跟徐宴說的話有誇張的成分在,但蘇毓心裡清楚,毓丫的這具身體虧損得确實很嚴重。長期的營養不良,造成頭發稀少幹枯,眼白渾濁,膚色黑黃。沉重的勞作和含胸縮背的習慣又造成了嚴重的頸椎問題和骨架錯位。
聽着好像都是小毛病,但積沙成塔,久了會牽一發而動全身。
不過蘇毓沒打算一口吃成個胖子,解決所有的問題。她現如今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補充營養。然後再不傷及骨頭的情況下,其次才糾正體态。
收拾了碗筷,蘇毓又去燒了一大鍋水。
别的她都不着急,但晚上一定得洗澡。在大冷天的,沒暖氣沒電熱毯的古代農村,洗個熱騰騰的熱水澡更有助于睡眠。
竈下火沒全蓋滅,留了點火星子。隻要稍微弄一弄就能着。蘇毓心道,稍微燒一下就有水,便不管了。所以,她洗完澡地就躺倒了。
徐宴從書房裡出來,已經不見蘇毓的人。問了徐乘風才知蘇毓進屋去了。
夜越來越深,門外的寒風呼嘯。冷氣從門裡竄進來,直往人衣裳裡鑽。徐宴拎着煤油燈進屋,順手合上了門。這大三間的主卧是沒有房門的,隻用厚厚的破衣裳料子縫制了一個簾子遮下來。徐宴掀簾子進屋,屋裡黑洞洞的。他将煤油燈擱置在桌上,扭頭就看到靠牆的炕上隆起一個背影。
擡腿走過去,蘇毓已經睡熟了。
徐宴:“……”自小到大,他還沒受過這等待遇。
以往毓丫都是先伺候了他們父子倆,再裡裡外外收拾一遍。洗漱後還得回屋縫縫補補一番,等他差不多睡下了才去歇下。偶爾天涼,還要送一碗蛋羹給他補身子。徐宴還是頭一回在家被冷落,别說蛋羹,就連洗漱用的熱水都沒有。
靜靜地看着炕上的人,那人一動不動,睡得很是香甜。
他有些不習慣,但也沒說什麼,罩着燈又出去了。
徐乘風早已困得睜不開眼了。他還是個孩子,年紀小,覺多。若是平日毓丫敢這樣,他定然要發脾氣吵鬧的。不過今日才被父親狠狠教訓過,他此時不敢吵鬧。
揉着眼睛,他跟屁蟲似的巴巴地問徐宴:“娘呢?她不去給我們燒熱水嗎?”
徐宴看了他一眼,自己提了個水桶去井邊,提水來燒。
十來年沒做過活兒,徐宴的那雙手每日隻需做做文章寫寫字,仔細算來,還真是十指不沾陽春水金貴公子。不曾親自做過也沒在意過日常瑣事,也是運氣不好。他這會兒搗鼓爐子,幾下一搞,徹底蓋滅了火星子。
徐宴:“……”他今日才發覺,生火也不是件易事。傍晚那會兒生了火還煮了稀飯,純粹是碰了運氣。
重新來,那就得好一番折騰。不知是不是故意跟他作對,折騰好辦半天,就是弄不着。
窗外的風越來越涼,竄進竈下擋不住寒氣。等徐宴生着了火,燒好水,已經是一個時辰之後的事兒。
這時候,徐乘風已經困得睡着了。徐宴看着撅着屁股趴在凳子上的兒子,沒有哪一刻像現在這麼清楚毓丫的利索和能幹。毓丫每日出門做活,居然還能回到家洗衣做飯一樣不落,真的是能幹。
心裡有些複雜,他将徐乘風送去側屋炕上安置,轉頭回到主卧門前又犯了難。
老實說,自從徐乘風出世以後,他便再沒碰過毓丫。甚至一年也進不了主卧幾次。但毓丫落水傷了腦子這麼大的事兒,他作為相公不聞不問确實有些過。他攜一身水汽進了屋子。站在炕前猶豫着要不要躺下,然後就看到一隻腳不客氣地踢出來。
鄉下的炕本就不寬敞,躺兩個大人剛剛好。但前提是睡姿規矩,不踢不打。徐宴看着炕上的人,蘇毓以非常不客氣的姿勢‘大’字型展開,絲毫沒給他留下腳的地方。
徐宴:“……”罷了,毓丫如今也不認得他,還是回自己屋去睡吧。
……
躺會床上時徐宴心中還有些納罕,怎地落個水就性情大變了呢?
憶起往日毓丫沉默寡言,說個兩句話都磕磕巴巴的樣子。徐宴歎了口氣,變了性子也好,有精氣神了,人也鮮活了許多。子不語怪力亂神,徐宴雖覺出蘇毓脾性變了,卻沒覺得毓丫被人換了芯子。
他歎了口氣,如今這模樣不像燒壞腦子,更像将腦子裡的水燒幹淨了。
一夜無話,各自睡下。
次日一天還沒亮,徐宴如常地早早起來讀書。
說來,徐宴年紀輕輕便才名遠播并非沒有理由。徐宴自幼聰穎異常,天生過目不忘。自開蒙起便展露出與旁人不同的自律和專注。這些年在學業從未有過懈怠,日日早起讀書,無論酷暑寒冬。
溫習了半個時辰,到了飯點兒往桌上一看。平日裡放吃食的桌上空無一物。徐宴有些恍然,這才從溫書中回過神來。憶起毓丫昨兒那陌生的樣子,徐宴不知為何笑了下。常年被人伺候慣了,這冷不丁得沒人伺候了,他還真有些不适應。
合上書,徐宴搓了搓凍僵的手,起身出去。
門一推開,白茫茫一片。昨夜不知何時又下過雪,院子裡又積了一層雪。越近年關,天兒便越發的冷。今日寒風又起,刮在臉上涼的刺骨。屋檐上的冰棱挂下來,天兒又冷了。徐宴下意識往竈房看,通常這個時辰毓丫都去河邊洗衣裳回來了。
不過今日顯然沒有蘇毓的人影兒。雪地上一個腳印都沒有。不必多想,這人怕是還沒起呢。
徐宴人立在屋檐下,一身青衣,清瘦修長的身影與皚皚白雪交相輝映,遠看着仿佛一尊活了的玉像。寒風拂動他鬓角的墨發,映襯得他一雙眼睛亮如星辰。左鄰右舍出來掃雪的姑娘婦人瞧見,不免都看得癡了。徐宴見慣不怪,遠遠地沖她們點個頭,踩着積雪往側屋去。
徐乘風也是這時候揉着眼睛開了側屋的門兒,他迷迷瞪瞪地邁着小短腿跨門檻出來。昨夜被父親狠狠打了手闆,睡前哭一頓,睡醒眼睛都是腫的。
這會兒瞧見父親,又忙喊了聲爹,哒哒地跑過來。
徐宴半俯下身替他整了整衣裳,牽着人去了竈下。昨兒傷了才子的自尊心,他一大早又來生火。父親燒火,徐乘風就遞柴。
燒了滿滿一鍋水,父子倆洗漱過後就回到書房,一邊教學一邊等蘇毓醒。
蘇毓一覺睡醒,已是日曬三竿。她還不知昨夜又下雪,隻覺得大早上這一會兒實在太冷了。手剛伸出被窩就冷的一哆嗦。在被窩裡賴了會兒,不知是心理作用還是當真昨夜的補藥有效,此時她覺得整個身體輕松了許多。她心裡一高興,一個鯉魚打挺爬起來去照鏡子。
昨夜睡前塗了厚厚一層藥膏,此時面上皴裂的凍瘡結了痂,已經不流黃水了。
雖然不流黃水,但看着還是磕碜。蘇毓趴在鏡子跟前仔細看過,估摸着不受凍上藥的話,應當能在十天内恢複。而且毓丫的這張臉,除了凍瘡以外,還有點地包天的去世。常年用嘴呼吸,含胸縮背造成的。索性不算太嚴重,還能修複。
心裡有了底兒,蘇毓幹脆不賴床了,穿了薄衫便開始在床上練瑜伽糾正體态。
蘇毓是練過瑜伽和體操的。常年伏案的人,都有圓肩和頸椎問題。蘇毓曾為了糾正體态,在這方面狠下過功夫。她不僅會瑜伽,健身塑性也很有一套。
就在蘇毓在床上将自己擰成麻花,徐宴許久不見她出來,掀了簾子進來瞧瞧。
然而剛踏進門就對上蘇毓冷汗涔涔龇牙咧嘴的一張臉。
徐宴:“……這是在作甚?”
蘇毓痛哭流涕,艱難地突出兩字:“正、骨。”
徐宴:“……”
這年頭還沒有正骨這一概念。但徐宴博聞強識,從字面上清楚地理解了意思。原來精氣神兒是這樣來的,徐宴嘴角一抽。想想,丢下一句‘悠着點’,轉身走了。
不管怎麼樣,萬事開頭難。
蘇毓的第一次做矯正嘗試十分痛苦,但在半個時辰的自虐下,蘇毓明顯有感覺到身上松弛了些。僵硬的脖頸和肩膀,她感覺身體狀況得到了改善。心情好了,這會兒看父子倆也順眼了許多。于是早飯她便也沒吝啬,将剩下的三個野雞蛋都煮了,一人一隻。
此時拿着一個白煮蛋的徐宴心情是複雜的。
徐乘風分到的蛋最小,嬌氣地翹着嘴要吵。被父親冷冷看了一眼,乖巧地閉嘴了。
昨日才買的米面,早上便吃的白米粥。蘇毓正琢磨着一會兒将藥材搗碎了洗頭,就聽到一旁徐宴開口。徐宴的嗓音當真是一大殺器,定力弱點的人都能被他迷得五迷三道。不過滅絕師太蘇博士很淡定,配菜喝着粥吃着蛋,聽得那叫一個三心二意。
這次回來便不用回鎮上。臨近年關,學院昨日便已經結課了。再開學,是來年三月份初一。另外,徐宴擡起頭:“束脩的事你不必忙了。明年我便不去鎮上書院。”
蘇毓一愣:“嗯?”
“學院的書我早已看過了,先生們也沒有可教的。”徐宴說得随意,“院長給了我一封推薦信,來年若無其他事,四月份去荊州城的南陽書院入學。”
蘇毓眨了眨眼睛,徐宴這情況,是不是相當于提前被保送去了省會重點高中?
這般蘇毓才想起來徐宴是秀才來着。十七歲的秀才,在古代算是鳳毛麟角吧……不過:“南陽書院不用教束脩?”
“你不必擔心,”徐宴瞥了一眼蘇毓紅腫的手,垂下眼簾,“我自有主張。”
既然如此,蘇毓就不操心了。
吃晚飯,她放下碗就又開始歎氣:“昨日去醫館,大夫說我這身子骨啊,這些年實在傷得太厲害。本來女兒家便不能輕易凍着,夏日不說,冬日裡涼水冰水之類的都是千萬碰不得的。咱家貧困,與别人不能比。我這常年冷水裡淌過來淌過去的,凍得手傷了實屬沒法子想。可如今,再不注意點兒,怕是傷及根本。女人傷及根本往後是要生不出子嗣來的,這也便罷了,壽數也得短上幾年……”
徐宴筷子一頓,看着她。
蘇毓的臉上凍瘡好了許多。不流黃水,紅腫也消了些。此時皺着眉頭,瞧着到有幾分可憐兮兮。
隻見她一臉的憂心:“我這手碰不得冷水的,碗筷怎麼辦,外頭那盆衣裳又怎麼辦哦……”
徐宴嘴角又一抽:“……都放着,我來。”
蘇毓擡眸看了他一眼,想下了,然後十分為難地點了頭:“那,就麻煩宴哥兒了。”
徐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