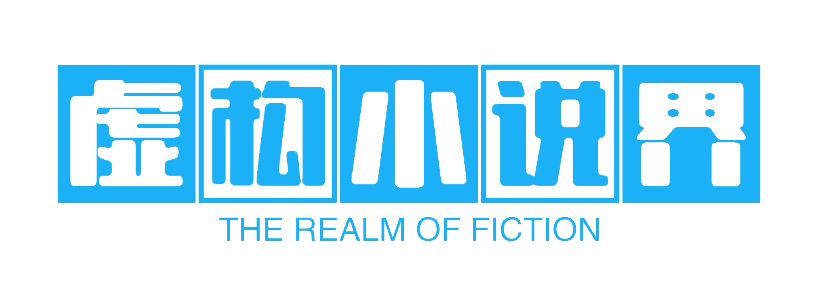第一百八十五章
第一百八十五章
人放了, 案子自然要查。徐宴不是以德報怨的人,但他素來信守承諾, 也隻能如此。隻是這件事答應得太憋屈, 以至于徐宴無論如何都吞不下這口氣。
“這件事結束以後,我不會放過他們的,”一手拿着傷藥一手仔細地替蘇毓擦, 眼睛緊盯着傷口, 不知在對自己說還是對蘇毓說道,“你莫要勸我。”
蘇毓瞥了他一眼, 神情淡淡的。
她倒也不是想勸, 畢竟遭罪的是她, 她蘇毓總不會以德報怨聖母到那個地步。隻是蘇毓到底是個現代靈魂, 或者說, 三觀早在現代便已經行成。她無法坦然地做到為了這件事背上兩條人命, 嚴懲可以,要命便沒有必要:“他們一開始便沒打算要對我怎樣。”
“我知道。”
徐宴低頭輕輕吹了吹傷口,見蘇毓身子輕微地顫了一顫, 他的臉色頓時難看。
“毓娘, ”他擡眸祥康蘇毓的眼睛, 難得嚴肅地告誡道, “善心是好事, 但有時候太過良善便會顯得軟弱可期。身為這件事,不給陳家兄弟的懲罰達不到一個殺雞儆猴的效果, 往後是不是府中所有奴仆都能效仿?是不是他們想讓你或者我做些什麼, 隻需要綁走府中的兩個孩子便可?你知我出身微末, 在這京城有多少人看輕你我?外面的人姑且不論,家中奴仆若管不住, 又方能護住你們娘三?”
蘇毓聞言沒有說話,許久,歎了一口氣:“嚴懲是自然,隻是,你一定要他們的命麼?”
這回輪到徐宴不說話了。
他抿着唇低頭去看蘇毓的脖子。陳子玉緊張之餘根本就沒注意力道,蘇毓的脖子上留下好長的一道傷口。徐宴安靜地盯着這個傷口許久,唇輕輕地抿着。燈光之下,蘇毓能清晰地看見他的眸色明明暗暗。若是陳子玉的手再往前多移動一些,就要割到蘇毓的喉嚨。
徐宴垂眸斂目,緩緩收起眼中的戾氣,淡淡道:“這樁事你不必操心,我會妥善處理的。”
話音一落,燭台的燈芯噼啪一聲脆響,火光乍現。
蘇毓看到徐宴眼中湧現的戾氣,不知該怎麼說。她沒有要放過陳家兄弟二人的意思,就如同徐宴所說。古代的人并沒有蘇毓想象得那般有腦子。這個時期的人受教育程度比較低,處于民智沒有太開的階段。并非蘇毓以學識論人,但一旦開了不好的先例,真的非常有可能會造成不可收拾的結果。
隻是蘇毓覺得,徐宴如今的戾氣比兩年前更重了。不知從何時開始,徐宴越來越有威嚴,但有威嚴的同時心性似乎也變得狠厲了許多。男子遊走官場,心性變化是正常的,但蘇毓還是希望他能保持初心。
“宴哥兒,”蘇毓忽然擡起手按在了他的腦袋上,輕輕地摸了一下,“心平氣和一點吧。”
……心平氣和?
徐宴心平氣和不起來。他人生在世就隻有蘇毓和三個孩子幾個家眷。往日與蘇毓不睦,他眼裡心裡便隻有乘風。如今夫妻和睦,子女雙全,徐宴怎麼可能容忍不相幹的人為了他們自家的糟污事累及妻兒?還是為這兩個白眼狼?憑什麼!
心裡如斯想,徐宴卻勾了勾嘴角,伸手将蘇毓摟進了懷中。
額頭抵着蘇毓的頸窩,深深地吸了一口氣。溫熱的氣息撲在頸側,帶着徐宴身上淡淡的清冽氣息。他沒有說什麼話,隻是臉頰微微蹭着蘇毓。
不知從何時起,徐宴就很喜歡這個動作。蘇毓從一開始内心吐槽翻白眼,到坦然接受并習慣他如此,漸漸摸索出徐宴的心思。他知道她在說什麼,也清楚自己這一年,或者說自從乘風身份轉變以後,自己心性上的改變。但徐宴無法說服自己停下來,他必須盡可能快地積攢勢力,将來才能更好地護住蘇毓母子。
“毓娘……”
徐宴笑了笑,不知是在說陳家兄弟還是在說自己,“我不會變成你想的那種人,但有的時候,人是需要為自己的行為付出一些代價的。”
蘇毓沉默了。古代不是烏托邦,她其實比任何人都清楚。
“若是有不要人命的方式殺雞儆猴,我還是希望你手上少沾染鮮血。”
說出這句話以後,蘇毓便沒有再勸了。
夫妻二人因這件事談過以後便沒有再談。至此以後,蘇毓身邊多了不少護衛,要貼身跟随。這既是徐宴的安排,也是白皇後的要求。至于陳家的案子,徐宴既然答應了,必然就會着手去查。
其實這樁案子并不難查,隻是涉案人員位高權重,壓着事情不放才總得不出結果。徐宴想查,說通了武德帝便迎刃而解。徐宴查案的速度非常之效率,何況這裡頭還有禹王和蘇家不少手筆在。當初草草結案是武德帝想護住禹王,如今他改了主意,自然是樂得徐宴揪出禹王更多的把柄。
徐宴一開口,武德帝想也不想就答應下來。
接下來的一個月裡,徐宴為案子忙得腳不點地。而關于李國夫人夥同蘇貴妃調換公主一事,武德帝給出了冷酷的處決。
李國夫人白清歡一杯毒酒賜死,蘇貴妃蘇芳被廢除貴妃的妃位,打入冷宮。其中涉案的蘇老太君早已去世,母債子償,蘇威蘇恒父子同時被革職。不過看在蘇毓親自替蘇恒求情的份上,并未沒收蘇家的家産。蘇恒的官職雖然被革除,但并未限制科舉。若是蘇恒走科舉一路,還有可能重返官場。至于林家,因為白清歡是主謀,林家付出的代價更大。冀北候府被收回,家财沒收,一家子貶為庶民。
哪怕老冀北候并不知曉此事,但古代便是如此,連坐從不講道義情理。老冀北候千裡迢迢入京,還不曾見到武德帝的面,替心愛的如夫人讨回公道便已經失了所有依仗。
不得不說,這件事對蘇林家的打擊非常之大,幾乎是毀滅性的打擊。除了蘇林兩家以外,武德帝借機也鏟除了一批他早就看不順眼的官員。任何威脅到他的存在,或者說讓他感覺威脅的,他一次性清除。
手段之殘忍,令人咋舌。
但白皇後似乎見慣不怪,這樣的事情其實已經發生不止一次。第一次是在二十七年前,巫蠱案,幾乎肅清了一半的朝臣和勢力。第二次是十年前的貪污案,這次是第三次。
“他手中握着一支見不得光的勢力,”白皇後不清楚這支勢力武德帝從何而來,極有可能是上一代傳到他手中。但總的來說,這是武德帝肆意妄為的底牌。明有内閣,暗有守衛,隻能說武德帝天生好命。哪怕是個庸才,也能守穩晉家的江山,“隻要他想,暗中的勢力可以為他做任何事。”
蘇毓想到了暗衛,影視作品裡總出現的勢力:“那是不是宮裡所有事都發生在陛下的眼皮子底下……”
“不會。”
白皇後很笃定,她太了解武德帝這個人了:“他沒花那麼多心思在這些事上。他那個人從來都是想一出是一出。再沒有危及他的利益之前,他絕沒有這等警惕心。”
蘇毓松了一口氣:“……”亡羊補牢型麼?這可真是太好了。
這一年,又是一年不平年。
蘇毓雖然不太清楚時政,但從商以後,對市場的敏銳度極高。她慣來也是個未雨綢缪的脾性。在得知了武德帝一系列行迹舉動以後,蘇毓心裡隐隐有一種不祥的預感。
有句話叫做獸窮則齧,雖然這般形容禹王一派有點古怪,但事實便是如此。當逼迫太過,必然會造成反撲。尤其晉淩钺蘇毓多少有些了解,此人心性兇戾,睚眦必報。某種程度上,融合了武德帝和蘇貴妃身上所有的優點缺點。換言之,絕不可能輕易便束手就擒。
心裡有這擔憂,蘇毓便張口說了。
白皇後聞言卻笑了:“不必擔心,他不敢。晉淩钺不過是個仗勢欺人的紙老虎罷了。沒有蘇貴妃在宮裡給他底氣,他根本不敢做這等事。況且,就算他有這個狗膽,他的手中也沒有兵。”
蘇毓聞言想了想,略微安心了些。當下便起身便告辭了。
與此同時,徐宴這邊将十年前的貪污案又徹徹底底翻了一遍。當初的案子确實判得有些草率。許多本該被處置的人因為各式各樣的勢力幸免于難,也有不少替死鬼含冤莫白。但很遺憾,陳家并不在此列。哪怕陳家兄弟聲稱陳主簿是被冤枉的,替人背了黑鍋,但他也确确實實貪足了銀兩。不然一個小小的主簿,哪裡有那等深厚的家底,夠他陳家在京中立足?
陳子玉看着查出來的結果,完全不能接受:“不可……不可能!不可能的!”
他堅信了這麼多年的事,證明是他想多了。他的父親根本死有餘辜,他們陳家也不過食民脂民膏而生的蛀蟲,這讓清高的陳子玉如何接受?
陳子安已經傻了,他一動不動地看着這些證據,表情是空茫的。
“你一定在騙我!”陳子玉面孔漸漸扭曲,唇上的血色已經全部褪盡了了。那種無法接受現實殘忍的掙紮讓他崩潰。他踉跄了疾步,忽地一手指着徐宴的鼻子,睜着一雙血紅的雙眼怒斥徐宴道,“徐宴你這個小人!你在污蔑我陳家的清白!你在公報私仇是不是!”
“信與不信,這便是事實。”徐宴對他的叱罵毫不在意,“一個主簿的俸祿有多少你應該清楚。你父親不過一個小小的主簿,何至于創出那麼大一份家業,你們兄弟二人自己掂量。”
丢下這一句,徐宴便不再與他們多話:“拿下!十年前案子的漏網之魚,不必姑息。”
護衛沖上來,在兩兄弟反應過來之前将人拿下收押。
這件案子從頭到尾不過一個月,結局出來的時候,就是蘇毓也忍不住咋舌和唏噓。她定定地看着徐宴,徐宴避開了她清澈的雙眼,握住蘇毓搭在膝蓋上的手蹭了蹭,有些邀功似的哼哼:“我并沒有親自去動他們。這件事秉公辦理……可還行?”
清悅的嗓音有種暗啞在裡面,搔得蘇毓耳廓一麻。
她低頭看着徐宴,忍不住笑起來:“那你是要怎樣?需要我獎勵?”
本身蘇毓這句話是調侃,在外早已威風凜凜的徐大人在家中還哼哼唧唧要獎勵。結果徐宴還當真不怕醜,應了這事兒:“嗯。”
輕輕一聲,蘇毓的心口劇烈一縮。
屋中的燭光搖晃,四月一到,天又熱了起來。主卧的窗戶是洞開的,窗外涼風徐徐,送進蛙聲一片。兩人依偎地坐在窗邊的軟榻上,蘇毓目光越過徐宴的發梢落到窗外的星空。星空一片璀璨,她鬼使神差地有了女子的柔軟,笑着開了口:“那宴哥兒,你想要什麼呢?”
徐宴低垂的眼簾下,眸光深沉得仿佛一團旋渦。
許久,他掐住蘇毓的下巴将她的臉穿過來,直視蘇毓的眼睛一字一句道:“我想要你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