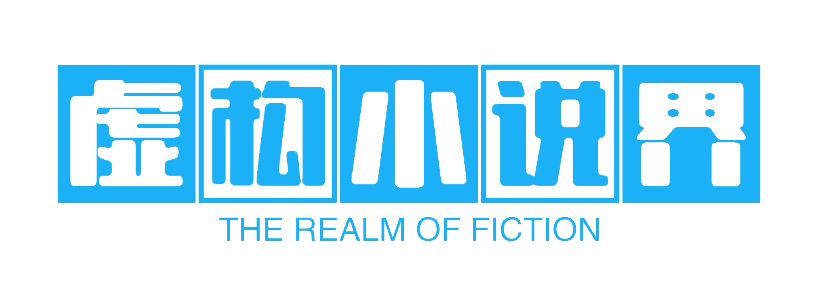杜媽陪着老伴住院到第二天,醫院再次安排杜爸做了幾項化驗檢查,第三天做了肝穿刺活檢手術。
肝穿刺手術後需卧床靜躺二十四小時,杜爸也遵醫屬,卧床休息。
杜媽焦急的等着結果,數次三番想打電話告訴女兒,又沒敢。
化驗結果在第二天才出來,杜媽再被請進專家醫生的辦公室,當聽到醫生宣布确診是肝癌,已經是肝癌中期,當時隻覺天都塌了,一陣天暈地旋,暈了過去。
醫生們反應過,将病人家屬給扶住,沒讓她摔倒,掐人中,一番急救将人掐醒,助理醫生又給病人家屬倒杯溫開水,讓她冷靜。
家裡的頂梁柱得了絕症,哪裡能冷靜下來?杜媽捧着紙質水杯的手直抖不停,連嘴唇都在哆嗦,她的大腦一片空白,像個木頭人似的坐着,兩眼沒有焦距。
醫生們見慣絕症家屬們的各種反應,也理解家屬在這種情況下完全無法自控的悲痛情緒,溫聲安撫,給家屬說就算是肝癌中期,也并不代表着沒有任何希望,讓她别太悲觀等。
對于醫生們的安慰,杜媽聽到了,可一個字都沒記住,茫然的坐了好半晌,空茫的眼睛才有焦距,眼淚如噴泉般的湧出來。
病人家屬情緒太大,醫護人員将她扶到辦公室外的等候區,讓她冷靜一下,以免耽誤别的病人來查詢結果。
杜媽呆呆的坐着,大腦混亂,坐了長達半個鐘,眼淚都流幹了,才慢慢的摸出手機,給自己的姑娘打電話。
杜妙姝在實習公司很努力,将自己的實習期當正式工作對待,兢兢業業,虛心好學,克己律己。
當天正值下午剛上班沒多久,工作中有電話打來,她看手機發現是自己媽媽,本來想不接的,因為爸爸媽媽在她工作時間内從沒打電放給她,這次忽然打電話,擔心家裡有什麼急事找,輕手輕腳的離開工作區,去衛生間的走廊接電話。
她跑到走廊,電話因超時也自動挂斷了,自己正想打媽媽電話,手機又來電,是媽媽再次拔号,忙接聽:“媽,我是姝姝,你和爸還好吧?……”
杜媽打第一次電話沒有打通,第二次重拔,當聽到女兒的聲音,壓抑數天的情緒崩潰,哇的哭了起來:“姝姝,你爸……你爸……”
她的嗓子啞了,哽咽着,幾乎說不出完整的話。
聽到手機裡傳來媽媽的哭聲,杜妙姝的心髒不受控制的亂跳,胸口好像被什麼東西壓住了,吸吸困難,媽媽很少哭,除非是受了冤枉,更别說号啼大哭了,媽媽的哭聲撕心裂肺似的,一定是爸爸出了什麼事。
她快站不住,腿在發抖,心慌慌的,拿手機的手也在發抖:“媽,你怎麼了,我爸怎麼,爸他怎麼了……”
爸爸究竟怎麼了?
被媽媽的哭聲吓得心中方寸已亂,杜妙姝驚慌失措,沒得媽媽的回答,再次催問:“媽,媽,媽,你先别哭,你先告訴我出了什麼事,我爸究竟什麼了?”
坐在醫院長椅上的杜媽,腦子裡亂糟糟的,聽到了女兒的話,她想說話,張了幾次嘴都發不出聲音,被一連催了幾次,又急又慌,嗚的哭了一聲,嘶啞着聲答:“你爸……你爸得了肝癌,姝姝,你爸他得了肝癌……嗚-”
杜媽說出那句話,好似用盡了力氣,發出一聲嗚咽,喉嚨又被堵住了,再次無聲的飲泣。
當“肝癌”兩個字鑽進耳朵,杜妙姝大腦裡“轟”的一聲巨後,再也站不住,兩條腿發軟,一下子就栽坐在地。
人坐了下去,眼淚也流了下來,手裡緊緊的攥着手機,想說話,嚨喉好像被扼住了似的,竟然說不話來了。
手機另一邊傳來的濁重的呼吸聲和無聲抽泣的噎氣聲,她知道是媽媽在哽咽,也聽到了些其他雜音,有人歎息,有人說“得了肝癌啊,難怪哭成那樣。”“唉,那種病就是必死病啊……”等等的話。
細碎的議論聲從手機裡傳來,杜妙姝的手髒像被一隻手扼着,呼吸困難,張了好幾次嘴,才發出聲音:“媽,你和爸現在在哪家醫院?爸他知道了沒有?媽,你先說說你在哪,我馬上回來……”
因為心裡的巨大恐慌,她在顫抖,牙齒都在打架,聲音也顫顫不平,她用盡了力氣才壓抑住沒有放聲痛哭。
杜媽聽到了姑娘帶哭腔的聲音,眼淚流得更兇,試了幾次,才控制住情緒沒有再次号啼大哭,顫着嗓子答:“姝姝,我和你爸前幾天就到省裡來了,就在市裡的人民醫院,我……沒敢告訴你爸,他現在還不知道……”
“媽,先不要告訴爸爸,我馬上就過去,我去醫院再說,媽,你等我啊,不要怕,我很快就過來,我到醫院了再打電話……”
自己心裡慌,但是,杜妙姝努力的讓自己鎮定些,爺爺奶奶是指望不上的,弟弟比她小好幾歲,挑不起什麼重任,爸爸出了那麼大的事,媽媽沒個人商量,沒個人可以分憂,她再不堅強點,媽媽一個人哪能承受得住壓力。
安慰了媽媽幾句,挂斷電話,低頭時才後知後覺的發現自己坐在地面,慢慢的站起來,手還在發抖,腿也是軟的,但是,她挺住了,沒有再栽軟下去。
杜妙姝拖着軟綿綿的腿挪步,每走一步像是走在棉花堆上,輕飄飄的,走了幾步才找到一點感覺,慢慢的從走廊走回工作部,将自己的桌面收拾一下,沒做完的工作也保存好,再去找帶領自己的負責人張經理告假。
張經理四十多歲,精英白領,在工作方面對部下的要求極為嚴厲,處理挺公正,頗受領導信任,也受部下信服。
見到實習生眼睛紅紅的,明顯剛哭過的樣了,猜着她必定遇到了很為難的事,聽說要請事假,倒沒為難她,問請假原因。
“經理,我……爸,在醫院,剛診出來……肝癌,我有可能要請多天假。”杜妙姝忍着眼淚,不讓自己哭。
“肝癌,确診了嗎?”張經理吓了一大跳,肝癌基本上可以說是絕癌,難怪女生一副天塌了的樣子。
“應該确診了。”
“那我先給你三天假,你去醫院了解了具體情況再論,如果三天假不夠,你再打電話給我說。”張經理沒再追問,大度的先開口給了假,想了想,又補充一句:“如果,還有什麼困難,你又找不到人可以請教,也可以在工作時間之外打電話給我,我不一定能幫你解決問題,也許可以給你一點點建議。”
“謝謝經理,我……先去醫院了。”經理對自己一直都很親和,杜妙姝心裡感激,深深的躹了個躬,後退了兩步才轉身,急沖沖的跑走。
女生和着眼淚跑出去了,張經理同情的歎口氣,過了一會兒才去工作部,将杜妙姝的工作交給另一位職員代替,要别人幫忙分擔工作,張經理自然也說明了理由。
也因此,接手了杜妙姝工作的員工知道杜的父親得了肝癌,閑聊的時候又說給同事們,同在一個部門工作的老員新員工也很快就知道杜妙姝的爸爸得了絕症。
從經理辦公室離開,杜妙姝拿着裝有私人物品的小包直接離開公司,下樓之後到街上,打車趕往醫院。
她報了地點,坐在車上一個勁兒的流淚,把司機吓了一跳,勸了好一陣,聽聞乘客的父親得了絕症,司機也不知該怎麼安慰了。
車開了一路,杜妙姝流了一路的淚,被送到了醫院的門診大廈,自己抹幹眼淚,付了錢,急沖沖的跑進大廈,再打媽媽電話,問清在哪,再一路找過去。
杜媽給姑娘了打了電話,坐在原地沒動,像個木頭人似的,想了很多很多,她和老伴其實都不到五十歲,因為生活困苦,做着又髒又累的活,所以看着出老。
老伴這麼年青就得了絕症,說不治,她無法看到自己的男人就那麼眼睜睜的等死,可要治,家裡就那樣,拿什麼錢來治病?
她家就兩個勞力,兩口子每天起早貪黑的做工,老伴還兼職了一份工,勉強能維持生活,今年女兒馬上畢業,眼看可以輕松一點點,誰能想到在這個節骨眼上,老伴又得了肝癌。
他們手裡積攢到的一點點錢僅夠兒子一年的學雜費用,這次住院也花得差不多了,哪怕公司有交保險,那也得以後才能報銷。
杜媽心裡像針紮似的痛,讓她放棄救自己的男人,她做不到,治病的錢又要從哪借?
她呆呆的坐着發怔,不知道坐了多久,聽到手機響,看到号碼是自己姑娘的電話,機械的接聽,機械的報了在哪個科室。
心頭亂紛紛的,杜媽挂了電話,捧着手機出神,坐了良久,直到眼前出現兩條人腿,她才茫然的擡頭看,看到了自己的姑娘,早已流幹的眼淚又一次湧出來,哽咽不成聲:“姝姝-”
杜妙姝依着媽媽說的信息,找導醫問了,準确的找到樓層,再找到某科室前,看到媽媽坐着發呆,心裡又痛又酸,跑到了媽媽面前,還沒叫出“媽媽”,眼淚先一步滾落。
當媽媽擡起頭來,她再也禁不住心裡的痛,蹲下身,抱着媽媽,嗚嗚的哭起來。
杜媽也抱住了女兒,也發出聲聲嗚咽。
母女倆抱頭痛哭,哭得肝腸寸斷,有幾位病人家屬于心不忍,走上前勸說安慰,給她們一些鼓勵。
人生沒有過不去的坎,說那句話安慰别人時容易,當真正成為被安慰的人,才知心中之痛何等深,面對無法跨越的災難是何等的無力。
杜妙姝哭得喉嚨發幹,哽咽着向來安慰自己的人道了謝,去衛生間洗把臉,再給媽媽擦了臉,鼓足勇氣走進醫生辦公室,咨詢爸爸的症情。
醫生接待了病人家屬,再次給病人家屬看影像圖,不厭其煩的就影像和化驗單一項一項的解釋依數據看病人哪些方面的情況比較嚴重。
肝癌已是闆上釘釘的事實,醫生與家屬讨論的是下一步有可能發生的事,比如癌細胞有可能快速擴散或者肝外轉移,如何治療等等。
杜妙姝忍着心痛不安,認真的聽醫生們對病情的分析和對治療建議,她不是醫學領域的人,不懂内行,保持傾聽,先不做決斷,先向醫生說她再找家人商量才确定具體的治療方案。
從醫生辦公室出來,她的腿比灌鉛還沉重,爸爸已經是肝癌中期,從活檢化驗與多項專項檢查論,癌細胞随時有可能擴散或轉移!
肝癌病人一旦進入晚期,基本上等于日子沒多少了。
爸爸已經處于很危險的階段,如果控制不住,有可能很快就發展到晚期。
醫生的話在腦子裡回旋,杜妙姝的腿重逾千斤,一步一步的從辦公室挪到外面的休息等候區,在媽媽身邊坐下,抓着媽媽的手,自己的手也在發抖。
“姝姝,怎麼辦?,我們該怎麼辦……”杜媽抓着女兒的手,又快崩潰。
“媽,還還有希望的,可以手術切除,還可以換肝……”杜妙姝手裡也慌,還得安慰媽媽,其實醫生說了換肝不太切實際,不說錢的問題,也不說手術是否成功的風險,僅肝源就是個大問題。
醫院裡也不乏等着換肝的病人,其中一個等了将近八個月還沒找到合符條件的肝源,一個等了半年之久了。
而且,杜爸本身條件也不是很好,換肝的風險與手術切除腫瘤一樣大。
杜爸的情況,做手術切除癌病竈也有極大的風險,有癌細胞的病竈區太分散,分散在整個肝葉的各個區域,所以目前隻能以介與治療或靶向治療、放療治療來控制病情。
醫生的分析讓杜妙姝感覺絕望,可她不能讓媽媽知道,隻能自己默默的承受着那份巨大的痛苦和煎熬。
有女兒在,杜媽有了依靠,聽了一通分析,心裡又有了希望,可是,剛生出那點希望火苗又下子又熄了:“治病起碼得要幾十萬,我們到那裡去借那麼多的錢……”
“……”杜妙姝也沉默,是啊,她們家是普普通通的家庭,湊個三五萬都吃力,何況是幾十萬?
錢不是萬能的,可沒有錢,萬事都不可能。
母女倆為錢發愁。
杜家沒有什麼富豪親戚,比較富裕一點的是杜爸的弟弟杜國勤,曾做過養殖生意,有三四十萬的家底。
杜妙姝也清楚的知道向叔叔借錢是借不到的,嬸嬸為人刻薄,叔叔一家不落井下石就不錯了,别指望幫忙。
也别指望爺爺奶奶,爺爺奶奶從她爸很小時起就隻偏心叔叔,什麼都向着小兒子,她爸隻讀了個初中就不讓讀書了,小叔不是讀書的料,爺爺奶奶硬是花錢将小叔叔送去讀了職高。
爺爺奶奶喜歡小兒子,所以爺奶給小叔建了房子,給小叔叔找了老婆,爺奶給她爸的是老舊的泥土破房子,她爸是自己找對象自己建房,一切都是靠自己。
杜家其他親戚也不是什麼有錢人,借個一二萬可能還可以,想多借點,親戚們也不一定願意借。
将自己家的親戚全篩選了一遍,杜妙姝也茫然無措,呆呆的發了會怔,默默的拿出手機,翻到了一個号碼拔打出去,回應的是千遍一律的“你所撥打的号碼已關機”。
樂小妞的手機仍然處于關機中,說明她還在閉關搞研究,還沒有出來。
拿着手機,盯着看了良久,又看了看時間,默默的撥打樂小妞的另一個号碼,那個她去首都讀書後新買的号,樂小妞閉關前有跟她說那個号交給她哥哥幫拿着,如果有什麼急事需要幫忙打另一個号碼。
晁家美少年打開學返校後很忙,每天都在東奔西跑,這一天,結束了下午的課程,開車準備去祭五髒廟,走到半路上手機響了。
任鈴聲聽就知是他家妹妹小可愛的手機,小團子閉關之前跟有聯系的人員說了要閉關研究,所以基本沒人打電話,逢年過節隻有信息或郵件。
有人打小團子的電話,想必是有什麼事,美少年将車靠邊停,拿出自家小可愛的那隻爪機,看是何方人士來電。
摸出的機子,看到來電顯示是“小肚子”,他便知是小團子小可愛高中唯一的朋友杜妙姝,看來電時間已有四十幾秒,趕忙接聽:“是杜妙姝同學吧?我是樂樂的哥哥,你找樂樂,是遇到什麼困難了嗎?”
所謂無事不登八寶殿,他也知小樂樂的同學小肚子沒事不會打電話,畢竟那個孩子在過年和西洋情人節那天都有給小樂樂的手機發信息,他也有回信息,代小樂樂回以祝福。
杜妙姝撥打了小同桌的号碼,心裡忐忑不安,當電話接通,聽到了溫潤如玉似的男音,尤其當最後那一句開門見山似的疑問入耳,她抑不住哽咽:“打擾你了,我能不能問一下,有沒辦法聯系到樂小妞?”
“杜同學,這個真的很遺憾,樂樂自跑去搞研究後再沒聯系我,也沒聯系她的那些保镖們,除非樂樂主動打電話,否則誰也找不着她在哪。”
晁宇博無奈的回了一個不太好的答消息,繼續問:“杜同學,你有什麼急事找樂樂嗎?可以先告訴我,即使我解決不了,我也能提供一些建議。”
“我……我……我爸……他得了肝癌……,我想找樂小妞幫我爸看看病……”杜妙姝原本不想說為什麼找小同桌的,樂小妞的哥哥聲音太溫柔,讓她無法隐瞞。
“杜先生得了肝癌?”晁宇博吃了一驚,趕緊的問下去:“确診了嗎?嚴不嚴重?你把所有化驗單和診斷結果掃描或者拍個照發給我,我拿去找樂樂的師哥看看。
肝病不能拖,我也不清楚具體怎麼治療才是最好的方案,我咨詢過專家再給你建議,治肝病也需要不少錢,你把你銀行卡發給我,我先從樂樂的銀行卡裡轉筆錢過去給你應急,你先别拒絕,這錢是樂樂借給你的,等你和你弟弟以後工作賺錢了再還給樂樂。”
杜妙姝聽着男生好聽聲音,聽着他主動問要化驗單找專家咨詢,還體貼入微的問要銀行卡幫轉錢,感激湧上心頭,眼淚似斷線的珠子往下掉,哽咽着連聲說謝謝。
“不用客氣,你是我妹妹高中時代唯一的一個朋友,是我妹妹的小姐妹,我要是連點小忙都幫不了,樂樂回來非得跟急。”
晁宇博聽着女生的哭腔,猜着她心裡難過,溫聲勸慰:“你别慌,吉人自有天相,我相信杜先生一定會化險為夷,你和你家人也不要擔心錢不夠,若是錢的問題随時打電話給我,隻請醫院用最好的藥,務必控制住病情。
你向醫生咨詢一下,看看能不能換肝,适合換肝就做換肝手術。”
“謝謝你,我問過了,醫生說我爸的條件換肝的風險太大,醫生并不建議換肝。”
“不能做肝移植手術,隻能針對性的治療是吧……”
晁宇博問了幾個問題,囑咐杜同學将化驗單拍照給他,挂了電話,先去吃飯。
女兒在打電話,杜媽沒吭聲,滿眼的希翼,當女兒打完電話,急切的問:“姝姝,你是不是跟你以前的同桌,就是那個送你弟弟鋼筆的同桌說話?”
杜妙姝搖頭:“不是的,我高中的小同桌搞研究去了,過年都沒回來,她的手機給她哥哥幫拿着,這個是她哥哥,小同桌的哥哥叫我将我爸的化驗單拍照給他,他去幫問問專家,還……代我小同桌借錢給我爸治病.”
“真的?你同桌的哥哥願意借錢?”杜媽激動的眼底浮出希望的火苗,有錢,就能給孩子爸治病,隻要有人在,錢是可以掙來的。
“嗯,同桌的哥哥說他幫我同桌保管着一張銀行卡,從我同桌的銀行卡裡幫轉帳過來。”自古錦上添花者有,雪中送炭者少,樂小妞和她哥哥是後者。
杜妙姝抹幹淨了臉上的淚迹,将裝在檔案袋子裡的化驗單一張一張的攤開,拍照,拍完了,再發往小同桌的手機。
她等了幾分鐘,同桌的哥哥回了一句“收到”,得到回信,将化驗單收起來裝進袋子,扶着媽媽去洗臉,再去看爸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