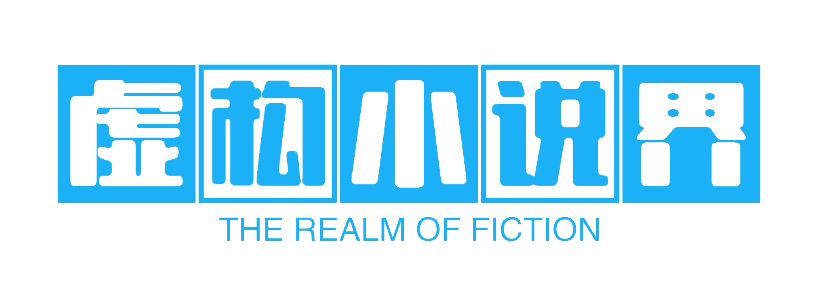第一百七十八章
第一百七十八章
甄婉為何會出現在這裡?如果她沒有記錯的話, 甄婉在兩年前就被送回了京城。蘇毓其實對甄婉沒有太多的恨,頂多隻是讨厭和厭煩罷了。
眼神瞥向徐宴, 徐宴捏了捏她的手指, 示意以後再說。
蘇毓于是也沒有多問,偏頭打量起甄婉。
老實說,甄婉一身紅甩着皮鞭的形象太深刻了, 此時看着梳着婦人發髻的甄婉說不出的别扭。兩年過去, 甄婉的模樣發生了不小的變化。原本還有幾分少女的稚氣,如今五官已然張開。已經十五歲的甄婉十分明豔動人。早前便知她是個美人坯子, 如今看來果然沒看錯。
此時矜持又安靜地立在跟前, 仿佛一幀仕女圖。
抿唇打量她許久, 蘇毓也沒說話。她心裡有些詫異, 不知這兩年甄婉到底經曆了什麼, 整個人看着似乎氣度大變。兩年前還嚣張跋扈的脾性此時收斂得點兒不剩。還别說, 甄婉如今的一舉一動竟然有幾分柔弱堪憐的味道。不過明豔的五官拖了後腿,硬裝的柔弱,總是顯出了幾分刻意。
蘇毓對甄婉這個人是沒什麼興趣, 當初在金陵起的沖突随着甄婉的離開都過去了。作為一個成年人, 總不會小氣到去記恨一個十三歲的小姑娘。若非甄婉是原書女主, 蘇毓或許都不會記得她。
不過這隻是蘇毓的心思, 甄婉心裡怎麼想那就不一定了。
事實上, 甄婉一年前便遠嫁栾城,其實對京中近來發生的事情知道不多。但當今長公主與國公府嫡次女抱錯的事她還是聽娘家人說過。畢竟甄婉曾經不知天高地厚地觊觎過大驸馬。貪圖大驸馬的美色, 膽大妄為地欺辱長公主, 企圖拆散長公主與大驸馬一家。
雖說這樁事到最後沒有成功, 甄婉也自食惡果,名聲盡毀。但龍子鳳孫可不是他們這等為人臣子想欺辱就欺辱的, 甄家人自然為此提心吊膽。
甄正雄的官職在一塊磚掉下來砸死十個人六個是官員的京城,不算是太高。他年紀上來以後,已經不指望能往上爬。如今就生怕蘇毓記仇,報複甄家和甄婉,将他往下拉去。不過一年過去,風平浪靜,并未等來蘇毓的報複。長公主好似忘了甄婉在金陵幹的那些事兒,提都沒提。
隻不過蘇毓不報複,不代表甄家心裡不忐忑。臣女以下犯上,皇後若是要折騰甄家,他們甄家也隻是螳臂當車,攔不住的。此時面對蘇毓,甄婉心裡七上八下的,生怕蘇毓突然想起來報複。
然而蘇毓隻是打量了她幾眼,便拍了拍徐宴的肩膀,示意他将自己放下去。
甄婉眼觀鼻鼻觀心,被蘇毓瞥一眼,她的頭皮都是緊着的。
徐宴從頭到尾都沒看甄婉一眼,隻抱着蘇毓往台階上走。觀兩人前後都是人,徐宴瞥到四周若有似無的目光,無聲地笑了一聲,将蘇毓放下來。
坐了将近二十來日的船,哪怕蘇毓不暈船,腳冷不丁踩到地上腿還是會有些軟的。在水上和在陸地上走,差别确實有些大。不過多走兩步以後就适應下來,蘇毓環着徐宴的胳膊與他一道去府。
這是一棟三進三出的院子,典型的南方建築,小橋流水。院子裡種了大批的竹林,竹林掩映,綠意滴翠。蘇毓擡眸打量了一下院子,什麼也沒多說。
夫妻倆剛走進院子,身後低着頭的甄婉快步跟上來。她如今身子抽條,纖細又高挑。細腰用了條紅腰帶掐得細細的,走起來搖曳生姿。不過不知是不是顧慮了蘇毓,方才還弱柳扶風很有幾分矯揉造作的走姿,此時倒是中規中矩了許多。
院子裡伺候的人不多,也就三兩個人罷了。這棟院子是賈林安特地撥出來給徐宴住的。徐宴的性子喜靜,除非必要的衣食住行,他不需要人跟前跟後。除了徐宴和廖原劉覓,沒有旁人在。
瞧了,蘇毓來的這幾日,廖原被徐宴派出去辦些私事兒,如今人不在院子。劉覓也在救濟營密切地盯着太醫。這個院子說起來,其實就隻有徐宴一個人在。今日是因為蘇毓到了。栾城的府尹賈林安夫婦沒敢去碼頭接人,就退而求其次,來這院子特地來迎接蘇毓。
穿過前庭剛走上長廊,從花廳的方向快步迎出來一個年輕的男子。
二十四五上下,一張輪角分明的國字臉,濃眉大眼,眉眼靈活,見人三分笑。他快步走過來便躬身向蘇毓行了一禮:“微臣賈林安,見過長公主殿下。”
蘇毓瞥了一眼徐宴,徐宴點了頭。蘇毓大緻便明白了,這位就是栾城的府尹。
擡了擡手,示意他起身:“起身。”
賈林安本身就是京城人士,隻是科舉以後外調來栾城當縣令。人雖然遠離京城,但家族勢力在,京中的動向他一清二楚。知道蘇毓是真正的金枝玉葉,姿态放得格外低。
蘇毓對識相的人沒什麼惡感,于是便順着賈林安的引路,一行人進了花廳。
夫妻倆剛坐下,仆從們便送上茶水。甄婉夫妻向蘇毓坐下之前,又想蘇毓行了一禮。蘇毓索性就問了賈林安如今的瘟疫情況。
這種病症自然是越早解決越好,早一日,便能讓多少人免于染病。
賈林安不清楚徐宴不願蘇毓插手這裡頭的事情,當下便将他知曉的情況一五一十地告知了蘇毓。蘇毓再三确認了病症以後,終于肯定了就是細菌性痢疾。可能會有一些别的并發症,但主要還是征兵。顯然她此次帶來的草藥都是對的,心裡便放下了一直懸着的大石頭。
甄婉從頭到尾在一旁安靜地聽着,倒是很有幾分溫婉柔順的模樣。
蘇毓放下心以後忍不住又關注起甄婉來。沒辦法,甄婉是原書的女主這件事,确實是蘇毓比較在意的。哪怕徐宴不喜甄婉,而甄婉已經成親。可千裡迢迢還能遇到的兩個人,蘇毓總是有點别扭的。
其實在栾城碰到甄婉徐宴也是始料未及的。他确實沒想到甄婉會嫁到栾城來,而且還是賈林安明媒正娶的夫人。不過時過境遷,早先甄婉做的那些荒唐事已經都過去了。徐宴作為瘟疫的主理人,該做的事情賈林安配合便是,倒也不需要跟甄婉打什麼交道。
若非今日蘇毓突然抵達栾城,甄婉又跟着他的相公來這處别院,徐宴都沒想起這個人。
蘇毓眨了眨眼睛,臉色一點一點冷淡下來。莫名其妙的,蘇毓有點在意起來。
劇情效應什麼的,她可不想遇到。
其實稍稍想一下就能大緻猜到事情的始末。不外乎,當初甄婉被設計污了名聲。被送回京城以後便匆匆嫁人。而她嫁的人剛好被外派到贛州來當縣令。蘇毓擡眸打量了一會兒這個二十三四上下的府尹賈林安,相貌普通,但一雙眼睛明亮而靈活。
雖然這賈林安的相貌不算太醜,但站在五官精美的甄婉身邊就十分的不起眼。甄婉那樣一個看臉的姑娘,怎麼最後選了一個平平無奇的男子做相公?
這般想着,蘇毓瞥了一眼徐宴。
當初甄婉名聲被污年紀輕輕便擇人出嫁根本都是徐宴的手筆。作為原女主的甄婉很可能至始至終都不知道,但蘇毓在面對甄婉之時,總忍不住會心虛。然而反觀當事人徐宴,反倒無動于衷。
兩人對視一眼,徐宴十分的坦然。
蘇毓:“……”
賈林安察言觀色,看到蘇毓的臉色冷淡下來不知出了何事。原本還想舉辦一場接風洗塵的酒宴,此時面上不由露出了幾分慌亂。
而他身邊的甄婉将腦袋低的更低了。以為她偷看徐宴的事情被蘇毓抓住,背後細細密密地起了一層汗。
屋内安靜了許久,水也沒有開口。
徐宴一看蘇毓的臉色就知她不高興了。他順着蘇毓的目光看過去,落到了低着腦袋的甄婉身上。關于甄婉,蘇毓在計較什麼,徐宴心知肚明。隻是從前在金陵的時候,蘇毓從未因他身邊的桃花表示過特殊情緒,難得蘇毓會有這等臉色,徐宴心中莫名高興。
眸子裡閃過淡淡的笑意,他淡淡地開了口:“罷了,你們退下吧。”
蘇毓不高興,剛好他也沒工夫應付這倆夫妻。他們夫妻已經大半年沒見了,他一個人孤身在外,相思男人。說句不恰當的話,香香軟軟的妻子送上門來徐宴此時恨不得将人大橫抱起,直接上榻。哪裡有那個閑工夫跟這些人扯那些心煩的事?
“長公主長途跋涉已經累了,”徐宴放下杯盞,看向兩人,“有什麼事往後再說,你們夫妻先回去吧。”
徐宴的話一落地,賈林安緊繃的心弦一松:“微臣還準備了洗塵宴,公主可要……?”
“不必。”徐宴拒絕,“殿下要歇息了。”
“那微臣先行告退。”說罷,賈林安便站起了身。
蘇毓淡淡地點了下頭,賈林安于是行了一禮準備告退。扭頭見甄婉還沒動靜,不着痕迹地扯了一把她的袖子,瞪了她一眼。甄婉不情不願站起身,兩人才匆匆告退。
人一走,花廳裡又靜下來。徐宴看蘇毓漸漸舒緩的臉色心裡很有幾分高興。
蘇毓無意當中瞥見他翹起的嘴角,忍不住翻白眼:“你樂什麼?”
“沒,”徐宴斂了斂嘴角笑意,“累了麼?要不要先去屋裡睡一會兒?”
自從接旨以來,徐宴每日密切關注婺城那邊瘟疫的情況。婺城雖說早在一個月前成了一座死城,但裡頭還是有不少人還在掙紮求生。切斷北上的路線是不得已而為之,徐宴卻做不到真正不顧婺城百姓的死活。栾城這邊糧食之所以緊缺,就是除了要養活栾城百姓,還得救濟婺城。
為了調度贛南幾個城池的糧食和草藥以及人手,徐宴每日都忙得腳不點地。接到蘇毓以後,他還得回到府衙去處理公務。但瞥了一眼難得過來的蘇毓,他有些舍不得走……
“不必了,”蘇毓沒看到他依依不舍的小眼神,倒是很想去救濟營看看,“我在船上早已睡夠了,再睡骨頭都要碎了。罷了,這就随你一道兒出去瞧瞧情況。”
徐宴聞言眼睛不由一亮。但轉瞬,又搖了搖頭:“你在府上……”
“你隻管去忙你的,”蘇毓打斷他道,“我有我的事情。”
徐宴冷不丁噎了一下,笑了。
正好這時候,蘇毓的行禮和仆從過來了。好多東西需要安置,蘇毓幹脆将人趕走。
徐宴無奈,再三囑咐了情況危急,這才離開。
他人走了,蘇毓立即将命人将準備的藥包發放下去。一些她根據現代理論命人趕制的防護用具,打發了仆從立即給救濟營那邊送過去。不僅如此,蘇毓還去了徐宴的書房。将她了解的關于細菌性痢疾的傳染源和相關知識,一一極盡詳細地謄寫出來。
然後吩咐仆從召集城中識字的書生謄寫這些注意事項。然後再讓栾城往來贛南各大城池的官府人員,将這些東西散發到贛南的各個城池,并想方設法敲鑼打鼓地告知不識字的百姓。估計是做生意營銷手段用慣了,蘇毓到了此地下意識地想辦法擴大防疫的宣傳。盡她的可能讓百姓清楚病情和傳播源,并能自己從自身做起,避開瘟疫。
蘇毓這邊忙着謄寫注意事項,碼頭那邊終于将蘇毓帶來的糧草卸貨完畢。
徐宴忙完了手頭的事情,還得命人親自盯着将東西妥善地安置。在這個瘟疫肆虐的時候,糧草很是金貴。特殊時期小人不少,若是盯得不嚴,指不定會少多少東西。
蘇毓的到來給疲憊的徐宴一劑強效的定心針。這厮嘴上說着讓人走,夜裡抱着人恨不得揉進骨頭裡。
日子一晃兒就過,眨眼就是一個月過去。八月初的時候,京中發生了一件小事。武德帝僵持許久硬是不處理的晉淩雲,被午門腰斬了。當着南陽王的面兒,香消玉殒。白皇後雖然厭惡了晉淩雲,但養了二十幾年女兒當真被腰斬,還很是消沉了幾日。
之所以這樣,都是武德帝這些人的錯。心中郁氣難舒,她看武德帝就越發的礙眼。正好近來蘇貴妃解禁了,又出來興風作浪。白皇後将那點惱火發洩到了武德帝等人的身上。
不知怎麼回事,武德帝這人似乎頗有些賤皮子。白皇後對他越冷臉,他反而越往上貼。
白皇後終究還是選擇先對武德帝下手。
此時姑且不提,就說蘇毓在宣傳完病情以後,瘟疫得到了更好的控制。徐宴不止一次地感歎娶妻如此,是他的幸運。蘇毓終于還是提出了要親自去救濟營。
“不行!”别的都可以答應,隻有這一條,徐宴無論如何都不能答應。
“不能再等了,”雖然染病的人差不多都死了大半,如今的瘟疫早已不成氣候,但這種病症總歸還是根除才好,“今年難道你還想在贛州過年?”
徐宴:“太醫已經研制出治療痢疾的藥方,不日便會有成果,你何必着急……”
“我自然有我的道理。”
明明藥方已經給出去,藥劑的配比也慢慢得到糾正,但還是有不同的症狀出現。原先蘇毓還覺得自己生化系的專業有些廢。但這一個月,她在高壓之下,連青黴素都折騰出來了。覺得實驗的過程中必定還是存在問題。禦醫們都是醫術高超,能力蘇毓不質疑。
問題出,定然就出在實驗的方式沒找對。若是當真因為這個耽擱了進程,蘇毓自然要站出來。
重複的話,徐宴不願多說。兩人為了這件事不知吵了多少回,徐宴就是不允許。蘇毓其實心裡也懂,徐宴不能容忍她犯險,但蘇毓總有一種預感,這件事就快結束了。
“我必須去,我能解決這件事。”
蘇毓其實有些生氣,她在這裡已經耽擱了一個月。就為了這件事,徐宴一直不能松口:“我不願跟你起争執,宴哥兒,你為何不能信我一回?”
“不行,”徐宴幹脆連道理也不講了,蠻狠道,“為夫說不行就是不行!”
“你以為能攔得住我麼?”
徐宴自然知道攔不住,蘇毓不是那種聽話的小女子。他可以在很多事情上講道理,就這件事上說不動。
“你可以試試看。”
這段時日,如膠似漆的夫妻倆難得因為蘇毓想去救濟營鬧了一場别扭。徐宴幹脆将府衙的護衛調來府中,命人将這院子層層把手,就是為了看住蘇毓:“你就在府裡呆着,哪兒也不準去!”
說罷,徐宴撇開頭不去看蘇毓眼睛,拂袖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