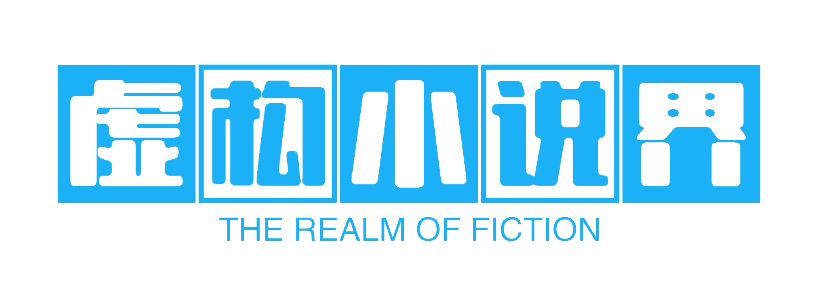番外之前世篇
番外之前世篇
是夜, 嶺南五河一帶。稷山素水鎮滇雲村。
素水鎮是坐落在稽山南邊的一個富庶的村鎮。面臨嶺南五大河,背靠稷山。依山傍水, 本是鳥鳴山間, 村民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安甯又富足。滇雲村在素水鎮的最南邊兒,靠山, 難得在如此深夜還吵吵嚷嚷。火把連成長龍, 從村頭排到村尾,将整個村子照得燈火通明。
尖銳刺耳的嬰兒啼哭聲, 或高或低的人聲仿佛在避諱什麼, 細細索索。混合着雜亂的腳步聲和呼喊, 所有人心都提到嗓子眼。伸手不見五指的黑夜為這個村子披上了一層古怪的陰森。
天幕黑沉沉地壓墜下來, 與遠處影影重重的山巒交接。擡頭一看, 頭頂不見一絲星光。雲層遮住了月色, 暗的深沉。砸無邊的黑暗下,擠擠攘攘舉着火把的村民将村尾的蘇家小院圍了個水洩不通。劣質的火把飄出煙灰籠在人群的頭頂,熏得人睜不開眼。
此時, 蘇家小院人群的最中央擺着一個香案。香案正中央擺着一隻香爐, 香爐裡點着香, 旁邊擺了一碟糖酥。如此寒酸的供品, 已經是這個村子能拿出來最好的東西了。
一個少女被被五花大綁地仰躺在地, 呼吸微弱,生死不知。
少女的兩隻胳膊被反剪着綁在身後, 膝蓋以下的腿不自然地扭曲着。散亂的頭發披在身後, 破爛的衣裳被井水打濕, 皺皺巴巴地黏在身上。纖瘦的身子因為痛楚在不停地發着顫,腰部以下衣裳啪嗒啪嗒地滴着水。定睛一看, 那水落到地上,紅殷殷的一片。
不必說,定是躺在地上那少女身上的血。血水蔓延,打濕了泥土。不過是眨眼的過程,她趴伏的那一塊地的泥巴都紅了。一張消瘦的鵝蛋臉此時白得像鬼,她半合着眼簾,氣息奄奄。嘴唇幹的爆皮,嘴裡不知在咒罵着什麼,無端滲人。
不知何時,似乎找回了力氣。她搭在地上的手指痙.攣似的抖動了一下,刷地睜開了眼睛。
兩條腿扭曲地折着,應當是被人打斷了的。冷汗順着她的額頭一滴一滴地滑下來,她一聲不吭。濡濕的頭發搭在前額,遮住了半張臉。發縫之中,一雙雙眼充血。不止是眼淚還是火光,她正透過濕漉漉的頭發正狠狠地瞪着眼前的一群人。
人群從中央散開,緩緩地走出了三個人。
最左邊黑皮粗手的短打中年漢子勾着腰,亦步亦趨地跟在一個穿着綢衣的老人身邊。這人正是這個院子的主人,也是她名義上的父親蘇大柱。右手邊打扮體面的綢衣老人,是滇雲村的村長。最中央為首的是一個和尚打扮的年輕人。俊眉修目,身形高大,與四周骨瘦如柴的村民格格不入。
如此炎熱的天氣,他一身幹淨的白色裟衣包的密不透風。光頭,高額瓊鼻,頭頂上卻沒有點戒疤。胸前挂着一百零八顆佛珠竄成的佛串,一副出家人打扮。他靜靜地凝視着地上的少女,表情無悲無喜。眼神似悲憫,又似冷酷,仿佛冷眼旁觀一隻掙紮求生的蝼蟻。
這人不是旁人,正是蘇家據說有仙緣的長子,也是素水鎮有名望的大師,蘇恒。
雖然是蘇家的長子,但十五歲被遊曆高僧帶走便與蘇家斷了年息。跟随老和尚修煉多年,老和尚身死道隕以後獨自返鄉,如今成了滇雲村推演避災的高僧,恒先生。
村裡人得了他的庇佑,哪怕他年紀輕,誰也不敢在他跟前輕易造次。
“誰準你這麼看恒先生!”蘇大柱眼疾手快,過去就是一腳。
這一腳踹在少女的腰窩,他腳勁兒不小,踹得人一聲悶哼。衆目睽睽之下,所有人都聽到‘咔嚓’一聲骨頭斷裂的聲音。村長卻搓着手,生怕好不容易來的活神仙被少女的不識好歹給氣走。點頭哈腰地道歉,扭頭又罵:“你這死丫頭給我在地上趴着!趴好了!”
鮮血又流出來,有那心軟的瞥過頭去,不忍再看。
在場人,誰也不敢說蘇大柱半句不是。畢竟這是蘇家養大的女兒。
蘇大柱沒注意蘇恒微微蹙起的眉頭,踢了一腳便收了腿。轉頭瞪了一眼立在一旁的蘇家婆娘。見她沒點眼色,就瞪着一雙眼睛巴巴地看着蘇恒,頓時沒好氣道:“瞧你這沒眼色的!沒看到村長和恒先生來了?還不快進屋端闆凳出來!”
蘇家婆子被他突然大聲給吓得一抖,反應過來,忙不疊地進屋搬凳子。
蘇家家貧,家裡也沒幾把椅子。她動作快,就将堂屋吃飯的那一條長凳給抱出來。似乎想跟蘇恒多親近親近,端着凳子便殷勤地放到他跟前。
蘇恒沒留心她,低頭看着地上的少女,手指一顆一顆地撚着佛珠。
蘇家婆娘沒得到蘇恒的注視,讪讪地退回去。
蘇大柱兩步上前,攙住村長的胳膊将人扶坐下。扭頭剛想去拉蘇恒。不過手剛一伸過去,被他自然地躲開了。他讪讪地搓了搓手,倒也沒介意。自從幾年前蘇恒回來便已經是這幅模樣,獨居一室,既不與村裡人來往也不與蘇家人往來。仿佛他們不是骨肉血親。
心裡有些難過,他殷勤地喚了聲蘇恒:“恒先生您快進來坐,快坐下。”
蘇恒并沒有搭理,淡淡地瞥了一眼蘇恒,擡腿走到了毓丫的旁邊。
他盯着少女的腿看,一言不發。他不說話,一旁的蘇恒卻漸漸心虛,急切地解釋道:“恒先生,并非我下手太狠。而是這丫頭太沒良心,半點不顧及村子的暗衛。能為喚醒山神出一份力,是她莫大的福分。她居然不聽恒先生的安排,連夜逃跑。”
“是啊,若非她實在太能跑,我們也不會動手。”蘇家婆娘湊過來,連忙幫腔。
蘇恒閉了閉眼,沒有說話。
蘇大柱與蘇家婆娘對視一眼,頓時有些慌。不知道他這幅神情是不是生氣了?
可是,看了一眼地上奄奄一息的少女,兩人心中不免覺得委屈。他們這麼做也是為了大家好。旁人不是蘇家人,不知道毓丫這死丫頭有多能跑。既然她是喚醒山神大人的關鍵,必然是不能跑的。毓丫這死丫頭若不打斷腿,那是誰也抓不住她的……
頭頂上夜色黑沉沉的,壓得人透過不氣。蘇恒不說話,在場誰也不敢說話。氣氛沉悶的仿佛凝滞,坐在闆凳上的村長,連呼吸都不敢太用力。
須臾,蘇恒吐出一口氣,擡頭看向了天空。
他安靜地凝視頭頂。村民們舉着火把,安靜地等着。有些心急的,也學他擡頭望天。
不知過了多久,雲層裡似乎有什麼動了一下,蘇恒的眉頭驟然擰起來。他手指快速地撥動着佛珠,複又瞥了一眼少女。頭發遮住了少女的面容,但在場所有人都知道這不過是一個十幾歲的瘦弱姑娘家罷了。這樣小的年紀,肩上承擔着一個鎮子的人命。
若非逼不得已,蘇恒也不想用這樣的方法。隻是如今這世道,朝廷無用,颙鳥現世。五河幹涸,再耽擱下去,這幾個村子上千條人命就要斷送在這次旱災裡……
他于是蹲下身,與地上的少女平視。
少女擡起了那雙充血的眼睛,似乎看清了面前的人是誰,她的雙眼瞬間盈滿了眼淚。此情此景之下,卻堅持不滾落下來。毓丫不明白,為什麼是她?素水鎮下是那麼多村子,村子裡有那麼多人。蘇恒想要讓一個人獻祭有那麼多選擇,為何偏偏是她?
她梗着脖子,毓丫一眨不眨地盯着蘇恒的眼睛。企圖從這雙疏淡的眸子裡找到半點不舍,畢竟是一起長大的。她還是蘇家為他養大的妻子,蘇恒當真就沒有舍不得?
但很顯然,他或許有愧疚,但并沒有絲毫的舍不得。火光中,白袈裟的和尚心存愧疚,隻是愧疚他對不起她。愧疚她的這一條年輕的生命,因為他的決定可能要斷送在這裡。
啞着嗓子,毓丫緩緩地開口:“……蘇恒,你就沒有什麼話要對我說嗎?”
他似乎歎了口氣,聲音很輕,一陣風過便散在了風裡。蘇恒斂起了眼中的神色,嗓音冷淡又理所當然:“阿彌陀佛,施主,貧僧法号慧濟,并非蘇恒。”
毓丫臉色一白,一滴熱淚滾落下來,眼中似乎有什麼東西碎裂了。
蘇恒眼睫微動,低聲念了句佛。
少女眨動了眼睛,忽然輕笑了起來。
不知是在笑自己的自作多情,還是在笑自己到了這一步還對蘇恒這個人抱有幻想。明明早已被疼痛抽幹了力氣,她卻哈哈大笑出聲。她想擡手給他一巴掌,卻因為雙腿已斷起不來。隻是在伸手的瞬間,被離得近的蘇家婆娘給按住了。
“你幹什麼!竟敢對恒先生不敬!”蘇家婆娘尖細的嗓音哆嗦地叫道。
毓丫卻仿佛不曉得疼,雙手向蘇恒的方向伸着,劇烈地掙紮起來。
她斷掉的雙腿在地上摩擦,越蹭越劇烈,血色無聲地蔓延。毓丫卻仿佛不知疼痛般堅持地要給蘇恒一巴掌。蘇恒蹲着沒動,神情無動于衷。
“你放開她。”
“什麼?”
蘇恒緩緩擡起眼簾:“女施主,請你放開她。”
蘇家婆娘一愣。張了張嘴,想說什麼。
蘇恒卻伸了手,将她撥到一邊去。
他挪了兩步,蹲到毓丫的面前,俯下身去。毓丫趁機便給了他狠狠一巴掌。
這一巴掌又恨又重,清脆的巴掌聲在蘇家小院響起,所有人都靜下來。蘇大柱喉嚨一哽,上前就想給打人的丫頭一個教訓。隻是他還未過來便被一隻胳膊攔住了。蘇恒擋在毓丫的跟前,高大的聲音将她遮掩起來。蘇恒的臉被扇到一邊,轉過來的瞬間,白皙的臉頰迅速紅腫起來。
“你以為挨了我一巴掌就夠贖罪了?你以為你這一巴掌,就能抵得上我斷掉的這一雙腿?”
毓丫惡狠狠道:“你做夢!”
“嗯。”
蘇恒擦掉嘴角的血漬,神情無悲無喜。
毓丫卻被他這無動于衷給激得雙眼泣血。她一把抓住蘇恒的衣領,揪着扯過來質問他:“這就是你要對我說得話麼蘇恒?這就是你所謂的教義?難道佛家教義是教你怎麼殺人不眨眼?怎麼背信棄義?你讓我等你十年,這就是十年後你給我的答案?!”
“你與貧僧終究是沒有緣分,早在十年前,師傅便已然斬斷了貧僧的塵世情緣。”
“蘇恒!”
“貧僧欠你的,貧僧會償還。”
“你償還?你拿什麼償還!”
蘇恒不說話了,垂下了眼簾擋住她通紅的雙眼。不論毓丫怎麼嘶吼,他都不置一詞,仿佛一尊沒有感情的佛像。
“今日所做之事雖是天命所歸,也是貧僧一人之過。女施主若是要恨,姑且隻記恨貧僧一人吧。”
他話還沒說完,少女一爪子抓花了他的臉。
撕裂的疼痛傳來,鮮紅的血順着臉頰滑下去,滴到了潔白的袈裟上。
場面頓時就是一靜,蘇恒怔怔地蹲在地上還沒動身。就看到身邊人影一閃,他擡手攔住又要擡腳踹人的村長,冷冷道:“不必,這是貧僧該受的。”
村長還有話說,但一對上蘇恒涼涼的眼神,所有的話都湮在了嗓子裡。
蘇恒沒有擦掉臉上的血漬,也沒有管臉上的傷口,任由他挂在臉上。潔白的袈裟上血迹點點,他低聲念了句佛便拿掉了少女揪着他衣領的手站了起身。旁邊的人都驚呆了。蘇恒自幾年前回鄉以後,從未有過如此狼狽姿态。這還是第一次,他衣裳沾了血。
無視了一旁蘇家人殷切的目光,蘇恒歎了口氣走到香案前。香爐裡的香已經燒到了半截,香灰落到香案上,擺出了一個古怪的形狀。蘇恒眉頭一皺,繞着香案快步走了一圈。
村民們不知他在看什麼,心都提起來。就見他繞着香案走一圈後,仰頭看着了天空。
無邊的黑暗籠罩着山岚和村落,天空連月色和星辰也吝啬照耀這片土地。火光映照之下,更顯得道路兩旁的樹木鬼魅與陰森。村民們不曉得他們到底在看什麼,隻擠在一起怯生生地看着他們。
所有人站在原地,戰戰兢兢的不敢有任何動作。火把将蘇家小院照得亮如白晝,卻并沒有給這些人帶來多少寬慰。站在堂屋的屋檐下扶着牆壁的老太婆偷摸瞥着蘇恒,又看了一眼地上倒在血泊裡的少女在偷摸地抹眼淚。毓丫這丫頭,她一直是當孫媳婦兒看的……
蘇大柱和村長等人面面相觑,屏息等着。
空氣中有甜膩的血腥味,不必說,是從地上的少女身上傳來的。
黃肌瘦的村民們安靜地等着,嘴裡嘀嘀咕咕地念着佛。有那不忍心的,聽到少女痛苦的呢喃隻能将腦袋扭過去不敢看,卻沒有一個人站出來為她說一句話。
“唉,造孽啊……”許久,終于還是有人忍不住小聲地嘀咕了一句。
“毓丫才十五歲,眼看着就要說人家,唉……”
“造什麼孽?這不也是沒法子想的事兒麼!若不是日子實在過不下去,誰又幹得出這等下地獄的事兒。”一個坡腳的老太太捂着自家孫子的眼睛,小聲地歎,“一會兒三年沒落過水了,五河的水都被烤幹。沒糧食,沒水吃,不請山神縣令,村裡孩子們都要活不下去了……”
“唉,就望着山神老爺能快些顯靈,快點将那等妖怪給趕出去。唉,可憐了毓娘年紀輕輕就要……”
“噓!噓!”這話還沒說完就立即被鎮長打斷,鎮長呵斥道,“又在哪瞎說什麼!”
“你可笑的恒先生在做法,絮絮叨叨地吵什麼吵!”他一手指指點點,疾言厲色地叱罵道,“女人家就是頭發長見識短,都到這個時候了還說這等沒用的。就是你們叽叽喳喳個沒完,到時候就你們家田不得庇佑,看你們還敢不敢嚼舌根頭!”
被村長這麼一吼,說小話的人頓時不敢多言了。
旁邊有村民趕忙附和道:“恒先生出家人最是慈悲。這麼做也為了咱們村,為了大家夥兒能活下去。隻要咱們山神醒了,殺了那隻妖怪,咱們鎮子就有救了!”
“再說山神是神仙。毓丫一個野丫頭能有這等機緣,指不定能長命百歲!”
“這可是旁人求都求不來的福分啊……”
“可不是?旁人哪有那等福氣嫁給神仙……”
“噓噓,都别吵了,再吵,擾得恒先生算不準就遭了!都别吵,閉嘴……”
……
細細索索的話時斷時續地傳到耳邊,蘇恒的眉頭皺得越來越緊。
村民們被他眼睛掃的心口一涼,頓時閉嘴,低下頭去。
蘇恒也沒開口斥責,他保持着隻是沒動,依舊是等。
天空陰沉沉的,似乎有什麼東西在動。一陣風緩緩地撥開了厚重的雲層,就看到被雲霧擋住的月亮漸漸地露出臉來。蘇恒擡起一隻手,手指快速地掐算。許久,他幽幽地吐出一口氣,冷聲道:“時辰快到了,快把人收拾幹淨,擡上山。”
說起來,素水鎮自三年前突然大旱。烈陽炙烤着大地,硬生生将五河稷山一代烤得滴水不剩,三年顆粒無收。如今餓殍遍野,瘟疫肆虐,村民為了活下去,易子而食。富庶的鎮子遭此大難,村民們上天無門下地無路,當真是别無他法了。
“是。”得了蘇恒的吩咐,村民們擡着一張步辇過來,七手八腳地将蘇毓擡上去。
這步辇是竹子新打的,料子很新,樣式簡陋。就是一把竹子的椅子兩邊扶手下面橫抻着兩根長竹竿。抻出來的兩頭和椅子的扶手兩邊都綁了紅繩子。打了結,有些不倫不類的。但這已經是滇雲村目前能拿出來最體面的東西。
毓丫姿勢怪異地趴伏在步辇上,或者說,架在步辇上。
那架勢不像是擡人,更像是綁畜生。兩條斷了的雙腿被硬生生拗正。雖然傷口已經不流血了,但這般來回的擺弄,早已沒辦法接。劇烈的疼痛刺激得毓丫幾度暈厥,冷汗一股一股地流下來。若是有那眼尖的人能看清,必然知道,她身上其實穿得不是紅衣。而是鮮血硬生生染紅了衣裳。
即便是疼,毓丫硬生生撐住了沒哼聲。
步辇擡起的瞬間,劇烈的颠簸帶動了斷掉的雙腿,她也依舊咬着牙沒昏過去。毓丫紅着一雙仇恨的眼睛是是盯着蘇恒的後腦勺,手攥着步辇椅子的扶手,用力到青筋暴突。火把的光映照在她的眼睛裡,她此時要将身邊這些人的臉一張一張都記到心裡去。
蘇恒自然感受到了目光,須臾,他到底是回了頭。
火光映照下,他清晰地看見這一雙漂亮的桃花眼,和眼睛裡燃燒着的熊熊火光與無邊恨意。心中忍不住一頓,蘇恒自己也說不清是什麼感受,隻餘下滿心的無奈。他走到毓丫的身邊,擡手捂住了她的雙眼,嗓音淡得像此時山澗的霧氣:“若是疼,且睡一覺吧。”
毓丫不知不覺地閉上了眼睛,眼淚汩汩地流下來,潤濕了蘇恒的手掌心。
他眼睫微微顫抖了一下,什麼也沒說。
步辇被擡起來,鮮血還在一滴一滴地滴落下來。血腥氣早已被風吹散,隻剩下滿地暗紅的色澤。蘇恒凝視着這血水,以及終于閉上眼陷入沉睡的毓丫,冷峻的面容有那麼一瞬的皴裂。但很快又恢複了冷漠。他手撥了撥手腕上的佛珠,默念起了幾遍清心咒,将這一股澀意壓下去。
素水鎮的大旱關乎整個村子四個村莊的人命。再不請山神出手,多少人命枉死。舍一人而救衆生,這是必然他要承受的罪孽。佛曰,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那且讓他來做這入地獄的第一人吧……
心中如此歎息,他手一揮:“時辰到了,上山!”
蘇家小院本就在稷山的山腳下。出了蘇家小院,多走幾步路便是稷山的石碑。皓月從濃厚的黑霧中出來,茭白的月色如流水傾瀉下來,為山道披上了一層白紗。
大旱三年,草木枯萎,沿途的樹木幹枯得踩下去便咯吱一聲化作腓粉。村民們分作兩批,将步辇夾在人群中央。前頭是年輕上有些力氣的年輕人開道,後頭跟着村裡的老弱婦孺。一個村子,七十戶人家浩浩湯湯地擡着昏迷的毓丫便上了稽山。
蜿蜒的山道像一條盤踞在山體四周的巨蛇,螺旋向上。
走了将近半個時辰,一行人終于來到了山頂。說來也怪,大旱三年,稷山這一帶滴水未降。按理說,應該草木蕭疏,枯木死灰。但怪就怪哉,山腳下的草木河流确實早已幹枯,就這稷山的山頂卻郁郁蔥蔥。樹木掩映之下,一條蜿蜒的小路出現在衆人眼前。
月色照着山澗,樹木影影重重,清晰地嗅到泥土的氣息。林中夜鳥呱呱聲,頗有些應聲。村民們面面相觑,頗有些不敢前行。扭頭看向蘇恒,望着蜿蜒的小道踟蹰地停下來。
“不必怕,”蘇恒冷聲道:“山中有神靈,樹木才久久不枯。隻管前行便是。”
村民們素來信他,擡着毓丫便匆匆走上了小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