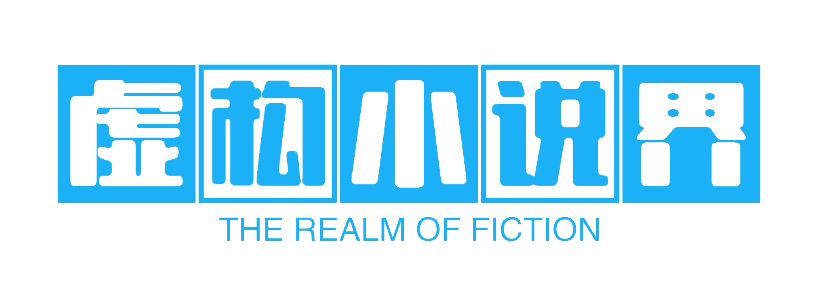第十七章
第十七章
昏暗的主卧,隻剩徐宴手中的煤油燈散發出昏黃的光。兩人一站一躺,靜默無聲地對視了許久。
蘇毓默默往裡側退了一點,退出他散發雄性氣息的影子包圍圈兒。雖沒開口說,但那拒絕的意思聰慧的人有眼睛自然看得明白。
徐宴一愣,倒是笑了。他今夜來此處,倒不是為了行那夫妻之事。事實上,兩人成親實打實算也有四年多,有過的肌膚之親卻少之甚少。
但兩人好歹是夫妻,徐宴雖然不大樂意跟毓丫同睡一榻,但過年前後這幾日卻是會在卧房歇的。以往四年就是這麼過來的,不過蘇毓如今忘了這默契,徐宴倒也沒拆穿她的誤會。
見她往裡躺了,徐宴轉身将燈擱到桌上,低頭吹滅才轉身回炕邊。四下裡安靜無聲,稍有一點動靜都清晰入耳。悉悉索索的衣裳布料摩挲聲,身邊一處被褥陷進去,蘇毓心口倏地一跳。
她抿了抿唇,翻過身去,縮在裡頭。一面唾棄自己為美色所迷一面又豎着耳朵聽。
心懸在哪兒,然而等半晌,沒見徐宴有什麼動作。
她悄咪咪伸頭看一眼,窗外的光照進來,蘇毓隐隐約約能看見男人寬大的肩膀和曲線分明的身形。呼吸聲是背着的。再一看,就見徐宴的臉朝着床外身子快貼邊兒了,已經睡平穩了。
蘇毓:“……”呵呵。
莫名噎了一口氣,蘇博士對他的後腦勺翻了一對白眼,也翻過身去。
與此同時,背對着她的徐宴眼睫顫了顫,沒有睜開。
一夜無話。
次日,蘇毓醒來,炕上已經沒人了。徐宴雷打不動的每日卯時起,在書房溫書做文章。即便是大年三十,他也沒有懈怠。不得不說,這厮強大的自律真是絕了。
堅持在炕上完成一套自虐的纖體操,蘇毓擦着汗便急匆匆去鏡子前照了照。
顯然昨夜的自作多情讓蘇博士的自尊心受到了些打擊,她憋了一夜,憋到現在可不就憋得難受?蘇毓趴在梳妝台前,左邊臉右邊臉都仔細瞧過。雖沒有養到令蘇毓滿意的程度,卻也已經稱得上美麗了。低頭再看看身材,胸脯不必說,腰肢比起之前細了不止兩圈兒,可以算窈窕。
前後看,左右看,她如今除了皮子粗糙一些,大小算個美人。蘇毓于是冷冷地得出結論:徐宴這厮要不是個性冷淡,那就是個睜眼瞎。
轉身拿了件襖子披上,她起身去竈房提水。
這一個半月來,她每日清晨提水擦身子已經成了徐家一家的習慣。因為蘇毓的要求,徐宴也習慣了每日早起洗漱完,留熱水給她。
提了一桶水進屋擦過,蘇毓又挑了一身簇新的襖子穿上。
色澤她特意選的豆青色,毓丫是黃皮,穿綠的顯白。仔細收拾了自己後,她站在鏡子前看着自己素面朝天的臉,心裡還是覺得氣不過。等那日有空了,她怎麼也得買一套胭脂水粉回來!
心裡那點小别扭,等徐宴從書房出來,蘇毓沒忍住給了他幾個白眼。
徐宴面上淡淡,心裡卻好笑。往日怎麼沒覺出毓丫的活潑?
顧及她臉面,徐宴穩穩地受了這些白眼:“昨兒那豬腸似乎鹵好了,今兒還做些什麼?”紅燒肉和糖醋小排收服了他的心,徐宴如今烹饪一道上知道蘇毓的厲害,權當自己是個打下手的。
鄉下人過年就得吃肉,将一年沒吃夠的肉一次性吃個夠。
蘇毓最擅長的就是做肉菜,憶起自己這一個半月以來少得可憐的吃肉機會,心裡頓時燃起熊熊烈火。有限的條件下,她要将能做的肉菜都做一遍!
“去将家裡腌的那罐子鹹菜抓一碗出來,做點魚吃。”鹹菜是毓丫腌的。毓丫做菜不好吃,腌鹹菜卻很有一手。老實說,這一個半月沒肉的日子,蘇毓有一半是靠毓丫的鹹菜撐過來的。腌的味道恰到好處,清爽偏酸,十分适合做酸菜魚。
鄉下肉貴,魚卻便宜。一來村口村尾都有河,想吃了去打就能抓到。二來魚刺多味兒腥,這年頭雖然有香料售賣,但大部分貧苦農人是舍不得花那個錢去買香料用,且就算買了也不會做。
這般兩廂攏在一處,魚自然就不值當幾個錢。
臘月二十七那天,村裡男人會打魚的翠香嫂子還特地送了魚過來。說是看望蘇毓受傷,當個新鮮吃。徐宴不會做,就拿水養在缸裡。這會兒蘇毓說要做魚,父子倆眼睛就看過來。
“魚也能做好吃嗎?”徐乘風往日吃過魚總覺得一股子土腥味,想起來都印象深刻。
蘇毓瞥了他一眼,公報私仇地惡意指使徐宴殺魚。
徐宴這雙手以前就隻拿筆,如今除了煮粥切菜洗衣服燒水,連殺魚都要幹。他此時立在院子裡,一身青布麻衣,與那夜初見時打扮一樣。沒化的積雪反射陽光為他整個兒罩上一層熒邊兒,他身姿筆直,與背後的皚皚白雪相稱,更顯得氣度清雅,姿态卓然。
此時聽到蘇毓說話,擡起眼簾。鴉羽似的眼睫半遮着眼睑,眸光陰翳,看人總有些似笑非笑的意思。
蘇毓理直氣壯地與他對視:“總得學會,不然以後豈不是隻煮粥?”
徐宴倒也沒反駁她,點點頭:“可。”
蘇毓挑了眉,就真的教起他殺魚。
老實說,每次教導他,蘇毓都有種智商上弱勢的憋屈。徐宴确實是第一次殺魚,但他的控制力和對事情的理解,讓他很輕易就掌握了别人要練習多次才能勉強上手的事。
魚殺得幹幹淨淨,沒留一片魚鱗,腮也清理得幹淨,連魚肚子裡的黑膜都撕得看不見痕迹。他清了三次水後,将魚整個兒規規整整地放在木盆中,人就在一旁不緊不慢地清洗手指。
蘇毓冷笑:“還不是不會生火。”
某從容的背影倏地一僵,徐宴扭過頭來。
“生個火生半時辰,”蘇毓微笑,“宴哥兒真的是能幹!”
徐宴:“……”
蘇毓揣着手轉身會竈房,準備一會兒做魚的香料。剛走兩步,又轉過身補一句:“對了,一會兒片也是你來片。我被人砸了腦袋,如今時不時手抖,拿不了刀。”
徐宴默了默,拿起帕子擦幹了手指,忍不住開了口:“你昨兒不是切過蒜?”
蘇毓:“……宴哥兒既然都學了殺魚,不若連片魚也一道學會。我觀有些貴人喜吃魚脍,宴哥兒将來是要高中的,總不能以後片魚都不會。”
……這二者有何必然的聯系?不過話說到這,徐宴也不多說點了頭。
還是那句話,徐宴這厮要是生在現代學了醫,妥妥的頂尖手術醫師。下刀都不帶手抖的,眼睛到哪兒刀就哪兒。蘇毓還是頭回見到第一次片魚就片得大小厚度一模一樣的人。母子倆蹲在砧闆旁,目不轉睛地看着他片魚,發出了由衷的贊歎:“你這手藝不去當劊子手,可惜了。”
徐宴:“……”
酸菜魚的魚肉要提前腌制一會兒,蘇毓将魚片先拿去腌,轉頭又準備其他的菜。
一家三口,不必做太多,大小八個菜過個年就夠。蘇毓是不喜歡吃剩菜的,八個菜,蔬菜至少占一半。這般兩頓少吃些飯也能吃完。
心裡盤算着一會兒的菜色。徐宴起身去側屋,拿了個銅盆,香燭,果盤和一袋子紙錢出來。王家莊有年三十吃飯前祭拜先人的習俗。徐宴雖然不信鬼神,但習俗還是會遵守:“毓丫忙得差不多就去裡屋收拾一下,我帶着乘風先去後山,你一會兒過來。”
蘇毓雖然不清楚這祭拜的習俗,但看他拿的東西也猜到了。看着材料配菜都備好了,擦了擦手去卧房換了身衣裳,扭頭也往後山去了。
她走得快,跺了跺腳,每一會兒就到了。
後山往日蘇毓跑得多,為了找點吃的,撿點柴火,總是要上山。她很清楚,因這山上有野豬活動,村裡人甚少在後山活動。這還是頭一回在後山看到這麼多人。
她眼睛虛虛一掃,就掃到了人群中鶴立雞群的徐宴。此時徐宴的香案都擺好了,帶着徐乘風在一旁等蘇毓過來。村裡那些婦人看到徐宴,眼睛就沒從他身上摘下來過。
蘇毓知道他受女子青睐,沒想到中年婦女也逃不出他的美貌。
有些好笑,她哈了口氣,剛準備從後頭繞過去。就看到一個頭上綁了藍布巾子的容長臉婦人拽了一下徐宴的胳膊。
她聲音壓得低,在問徐宴:“聽說毓丫這幾年熬幹了身子?大夫說有礙子嗣。宴哥兒啊,大過年的不是嬸子說那喪氣話,這女人生不了孩子就是那下不了蛋的雞,養着也是白費糧食。你還年輕,前途遠大,可想停妻另娶?就算不停妻,再娶一房也是好的。”
徐宴的臉色冷淡下來,抓着徐宴袖子的徐乘風眨巴了眼睛,沒聽懂。
那婦人也不曉得看人臉色,自顧自地繼續說:“我家桂花明年也十六了。按理說早該說人家,但是這孩子你也知道,有些怕生,被人吓唬兩聲就不敢出門。”
“這不,年前議親被人家小夥子吓唬一場,躲在家裡不願出門了。”
她歎了一口氣,一幅給人占去多大便宜的态度,“别的我也不自誇,我家桂花那大屁股,那水靈靈的臉蛋兒。誰人見了她的不誇一句是個好生養的?嬸子不圖啥,就圖你品性好,知根知底兒。宴哥兒啊,你往後多疼愛些,我家桂花給了你做小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