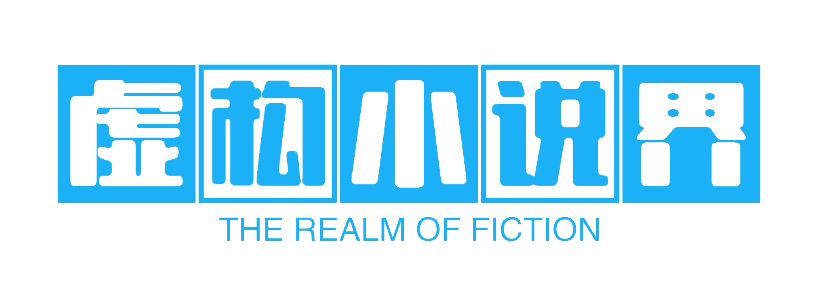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四章
蘇毓這話一出, 場面頓時就是一靜。
顯然,在場誰也沒想到蘇毓會提出這樣出格的要求。二十兩銀子不是二兩銀子, 況且, 即便是二兩銀子,也足夠買這婦人的幾百張卷餅了,這婦人居然敢當衆獅子大開口。且不說, 蘇毓的一番話把甄家的人和同行的車把式都吓白了臉, 就說甄家的護衛此時看蘇毓的眼神也不亞于在看搶匪。
徐宴微擡眼簾瞥了一眼蘇毓,蹙起的眉頭平整了, 複又安靜地坐了下去。
甄婉倒是沒覺得蘇毓在獅子大開口, 她隻是被蘇毓強硬的态度給激怒了。這是個什麼上不得台面的鄉下婦人?甄家打賞下人, 十兩二十兩眼眨不眨地就給了。此時就當是在打發下人了。心中鄙夷蘇毓眼皮子淺, 她想也沒想就冷笑:“三十兩, 加十兩給她!那十兩算是本姑娘賞給她的!”
仆婦聞言臉色蓦然一僵, 似乎沒料到甄婉是這個反應。别說她,就是蘇毓這邊的幾個人也被甄婉的反應給弄驚了,不敢置信地看向了甄婉。
甄婉卻昂起了下巴, 一臉的倨傲:“本姑娘, 賞給你的。”
說着, 她一個利眼瞪向了仆婦。仆婦不敢耽擱, 連忙去後頭拿了一個荷包給蘇毓。
蘇毓也沒跟她客氣, 廢話,當然不會跟她客氣。沒有人跟錢過不去, 尤其是傻子的錢。于是接過來就當着甄家人的面打開來了。裡面不多不少, 正好三十兩。
錢到位, 一切都好說。蘇毓也不跟她廢話,将這卷餅就讓那仆婦端走了。
天知道仆婦端走吃食是那咬牙切齒的模樣有多好笑。但甄婉看到那噴香的卷餅呈到她面前, 漂亮的小臉兒上露出了志得意滿的笑容。
蘇毓看着甄婉挑剔地嘗了一口餅,自己到沒覺得如何,徐家這邊吃飯的幾個人放下了碗筷。
車把式吃得快,三兩下就嚼了一個餅。這會兒空着筷子,見女主人蘇毓忙活了一場什麼都沒吃着幹巴巴地直撓頭。徐乘風小屁娃子悶聲不吭地看了眼自己碗裡啃一半的餅,又看一眼蘇毓,小眉頭皺起來。似乎在猶豫要不要将剩下的一半分給蘇毓,想給,又舍不得的樣子。
徐宴的餅也吃得剩一半停了筷子:“我再去剪兩節香腸過來?菜葉子還要嗎?”
蘇毓掂了掂沉甸甸的銀子,對自己一個手抓餅賺三十兩十分滿意。并沒有在意甄婉的眼神,很是自在地點了頭:“多剪幾節肉腸過來,還剩十來張餅呢。”
徐宴點點頭,放下筷子就往外頭去了。
那邊吃着三十兩買來的卷餅的甄婉見蘇毓對她的羞辱無動于衷,頓時就有些不滿意了。尤其是見那清朗俊美的男子不僅沒因這婦人貪婪的嘴臉厭煩于她,還貼心替她去拿吃食,心頭又不舒坦起來。吃在嘴裡鮮香刺激的餅失了滋味,她嚼了兩口,突然将碟子往旁邊一丢,不吃了。
碗筷與碟子碰在一起噼啪一聲,那邊的一行人絲毫沒因她不悅誠惶誠恐,甄婉突然拔高了聲音道:“這是什麼低劣的吃食?吃進嘴裡都割得我嗓子眼兒疼!不吃了,給你吃吧!”
說着,将碗碟往仆婦手裡一撥,意思是要仆婦吃。
仆婦哪裡敢違背,隻能接過去吃。
甄婉說完這番話就拿眼神去瞥蘇毓,見蘇毓還是對她的動作無動于衷,心裡就不由壓了火。甄婉自小到大被甄家上下捧在手心裡的,含嘴裡怕化了,碰一下怕摔了。平日裡皺個眉頭,都能叫下面人跑斷腿,别提這麼明顯的鬧脾氣了。結果出了京城走出甄家以後接連的受氣,受苦,受累,心裡當真是委屈的要命!
她剛想說點什麼刺激一下蘇毓,就見自己這邊幾個護衛叽裡咕噜的,居然有一個起身走到蘇毓的身邊。就是剛才拿匕首吓唬她的那個絡腮胡大漢,居然好聲好氣地跟那個鄉下婦人商量,拿銀子買她的餅子。
“可否便宜些?”方才這婦人開口就要二十兩,他們也是聽在耳裡的。雖說有甄家這小姑娘事事咄咄逼人的原因在,但總的來說,他們想吃一口香的也有些膽戰心驚。不過路上辛苦了一路,嘴裡淡出個鳥了,還真就圖這一口吃的,“我們哥兒幾個多買幾張餅。”
誰知蘇毓萬千沒有方才難說話的态度,很随意地就點了頭:“你要幾張?”
“來八個行麼?這是銀子。”那漢子瞥了一眼油紙包住的餅子,不确定地遞過來一個荷包道。
蘇毓接過來看都沒看就點了頭:“可。”
她這般态度倒是叫漢子有些尴尬了,這婦人原來是個暴脾氣的性情中人。
說句實話,本來這蔥油餅就烙了不少,真要吃的話,一家三口吃個飽能吃個四五頓的。但在蘇毓看來,手抓餅這種東西也就吃個新鮮,天天吃腸胃也不好受。左右沒幾日就到金陵了,還有好些凍水餃沒吃。這些蔥油餅能換了銀子,也算是一件意外收獲。
蘇毓動作很快,徐宴剛拿了東西過來,她三兩下就出了一盤子餅。
三個手抓餅一端上去,蘇毓特意刷夠了辣醬和鮮肉醬。鮮香麻辣的味道在舌尖兒炸開,壯漢的眼睛蹭地一下就亮了。壯年漢子都是西北駐軍,口味重,就好這一口鹹香。蘇毓露的這一手雖稱不上驚豔,但就是抓勞了這群漢子的點兒。
味兒香,又燙,咬下一口都是享受。
說好八個餅子,蘇毓沒一刻鐘就做好了。
漢子們吃的也快,圍在蘇毓的火堆旁邊等着吃,蘇毓前手剛做好他們後面就吃完了。甄婉見狀臉都能氣通紅,甩着手,撒火似的打翻了仆婦的碗碟。一群人聽到動靜立即看過去,她漲紅着臉頰便叱罵:“看什麼看?沒看到大戶人家教訓不懂規矩亂吃别人家東西的奴婢?”
正吃着蘇毓煎的餅的幾個壯漢嘴一僵,十分尴尬。嚼在嘴裡的餅是吞下去也不是,吐出來也不是。幾個漢子被噎得難受,但到底顧及甄正雄的面子,隻能對甄婉的指桑罵槐裝聽不懂。
徐宴微微掀起了眼簾,淡淡的目光仿佛不經意瞥過去。
也不知怎地,罵人的甄婉便立即止住了訓斥。她好似個高貴的世家貴女,微微昂起了下巴。驕矜中略有些嬌羞的目光投回去,這邊徐宴已經又低頭不看她了。
甄婉被這一眼看的心花開,心裡跟被貓爪了似的,癢得厲害。
她總覺得,眼前這個公子對她是有那麼點意思的。若非心有念想,為何要多次偷看于她?且次次被她抓住了。甄婉沒嘗過這等抓心撓肝的滋味兒,隻覺得冥冥之中妙不可言。她忍不住想,看這公子的衣着,顯然是布衣。布衣的話,這公子的出身必然就不可能會顯赫。
一介布衣,是無論如何都配不上甄家的姑娘的,就算這公子生的一副好相貌,也不行。況且,這公子還有了妻子兒女,早有家室。
但即便如此,甄婉又瞥了一眼那邊的火堆。徐宴安靜地做在其中,顯得如此的卓爾不群。唔,她也并非不能給這位公子留下一點念想。
心裡遺憾,将目光投向徐宴。
隻是盯了許久,再沒碰上徐宴的目光。甄婉忍不住對蘇毓遷怒,于是看這幾個護送的人就格外的刺眼。
蘇毓對甄婉心中如何想不知,她隻知道煎完餅就可以弄自己要吃的。指桑罵槐也好,那都是别人家自己的事情,跟她一個外人可沒關系。不過賣個餅,再說,她自己的肚子獨自還空着呢。趁着幾個壯漢臉色難看地吃餅,她扭頭問徐宴:“你一個餅夠了嗎?”
事實上,别看徐宴生得清瘦,實則脫了衣裳渾身的精肉。十八.九的少年正值長身體的時候,徐宴又比旁人高出許多,自然最是能吃。一個餅,就算夾了肉和蛋,也是不夠他飽腹的。
此時既然蘇毓問了,他便老實地點頭。
正好蘇毓不想吃餅就道:“那行,就這湯水一人再下一晚水餃。”
一碗水餃下肚,蘇毓也吃飽了。忙活了一場,掙了四十七兩銀子。三十兩是那姑娘上趕着送來的,十七兩是幾個漢子給的飯錢。蘇毓頭一回發現銀子這般好掙,要知道,這年代一兩銀子可是相當于現代兩千二百多元的購買力。四十七兩算是不小的一筆收入。
冬日夜裡冷得厲害,徐乘風吃了半張餅就飽了。此時靠在蘇毓的身邊,歪歪栽載地打着瞌睡。蘇毓其實也有些累了,吃完飯就帶着徐乘風去後頭騾車裡擦洗,刷洗碗筷的活計自然是交給徐宴。
徐宴對此也沒有怨言,端着油污的碗碟便走出了破廟。
這會兒天色已經全黑了。沒有月亮的夜裡便格外黑,伸手不見五指。本來刷洗碗筷不必走太遠,畢竟大晚上去水邊也不安全,油污若是用冷水也洗不幹淨,便想着用方才燒的水刷洗一下。但這會兒徐宴瞥了眼鍋裡,熱水被蘇毓端去了騾車,沒剩下的。
想着一會兒許是要用,他于是又放下碗筷去騾車那邊拿桶,裝些水回來燒開。
徐家人離開,甄婉就又跟同行的人鬧起來。
不為其他,就為這幾個漢子居然當着她的面兒去買蘇毓的吃食。方才徐宴在,甄婉不好當着徐宴的面兒展露脾氣暴戾的一面。随說早在她鬧脾氣遷怒蘇毓母子之時,徐宴就不可能對她有好印象。但甄婉素來不覺得自己會做錯事,在甄家,錯的永遠是下人。
所以,徐宴人一走,她忍不住就借題發揮,又鬧起了脾氣來。
四個護送她離京的士兵早就受夠了這姑娘的稍不順心就鬧脾氣,這會兒見她鬧騰,絡腮胡漢子就忍不住又拿出匕首吓唬她。甄婉雖然被匕首唬了那麼一下,但打心裡不覺得這群人敢忤逆她。
一怒之下,她甩了袖子就跑出了破廟。
這荒郊野嶺的,甄家幾個護送的人也煩了。護送甄婉的幾個人明面上是甄家的護衛,實則個個都有官身的。軍籍雖說不夠高,但也大小是個官。料定甄婉那性子欺軟怕硬,惜命的很,定然不敢一個人跑出破廟太遠。于是也堵了氣,不管甄家的仆婦如何求,就是一個都不出去找人。
這一賭氣,他們不曾想到甄婉當真敢跑出破廟。不僅如此,她還拎着裙擺往林子深處跑去。
與此同時,徐宴拎着水桶不緊不慢地來到溪水邊。這水是他之前找到的,雖說小溪離破廟有些距離,但水質甘冽清甜。不說燒來用作洗碗筷的熱水,留着明早煮粥也是好的。
正當他彎下腰汲水,就聽到不遠處噗咚一聲,有什麼東西一腳踩空,落水了。不是落他跟前的水,似乎離他這裡有點距離。但夜裡很靜,動靜着實有些大。
徐宴心中一凜,以為是遇着什麼野獸。汲滿了水便拎起水桶立即就走。
隻是他方一轉身,就聽到了清晰的呼救聲。那聲音由遠及近,又好似瞬間飄遠。總之,大晚上聽着格外的滲人。徐宴不願多做糾纏,腳下的步子都邁開的大了一些。可能是他突然之間稍微有些慌了神,夜裡又瞧不清楚路。走着走着,他走到了一個不小的深潭邊上。
這呼救聲就清晰地傳入耳中,也不知是不是湊巧,一陣風吹開了雲霧。森冷又茭白的月光照下來,他清晰地看都潭水中央一個撲騰的人影,巨大的水花和大動靜,安靜的林子裡,回蕩着女子驚恐的呼救:“救我!救命!求求你救命啊!”
這個人不是旁人,正是破廟裡那個貴人小姑娘。
徐宴拎着水桶冷眼看着她,許久沒有動靜。直到甄婉被凍得腿腳發麻,衣裳吸飽了水正在往下沉,他才緩緩放下了水桶,不慌不忙地脫了外衣。
倒春寒的潭水比溪水更冰冷刺骨。徐宴遊到潭水中央勾住了撲騰人。隻是他才勾住,水裡那人的手腳就八爪魚似的纏上來。邊纏邊将自己的人往徐宴的懷裡頭鑽。徐宴被纏住了手腳,遊得特别慢。好不容易遊上岸,差點沒将自己凍死在裡頭。
被救上來的小姑娘哆嗦着還往熱源貼,嘴裡一個勁的喊冷。
徐宴被纏得快不能呼吸,伸手狠狠地将人撕下來丢開,臉都發青了。
他下手幹脆利落,沒有一絲一毫的顧慮。這般毫無憐惜的動作卻叫甄婉猝不及防的同事,意料之外又心口大震。她意識到徐宴有可能對她沒什麼心思,但她看着眼前高挑挺拔的人。自幼長在京城,與甄家家世相當甚至家世越過甄家的男子對她從來都是小心翼翼的,甄婉人生裡還是頭一回遇到對她不屑一顧的人,尤其這個人皮相出色到鳳毛麟角,讓她心神恍惚,幾種情緒雜糅在一起,她忽然對徐宴興趣大增。
徐宴這個人在她心中的印象一下子被拔高了。她此時盤腿坐在地上,仰頭注視這神情冷冽的徐宴,不知在想些什麼,目光竟十分的癡然。
正巧姗姗來遲的甄家護衛就看到了徐宴冷冽的表情和地上哆嗦的甄婉。
緊跟上來的仆婦趕忙将一個大麾罩到甄婉的身上,張口就想對徐宴破口大罵。但是還未開口,便被甄婉厲聲喝止了。甄婉籠着大麾緩和了好久才緩過神來。身子暖過來,她嘴唇還是烏紫的,但盯着月光下輪廓仿佛被月光描出一層熒邊的徐宴灼灼如火。
她咳嗽了許久,歪靠在仆婦的懷中對徐宴道:“小女姓甄,單名一個婉字。多謝公子今日的救命之恩。不知公子尊姓大名?往後小女好登門緻謝。”
“不必了,順手為之罷了。”徐宴穿上外衫,拎着水桶便轉身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