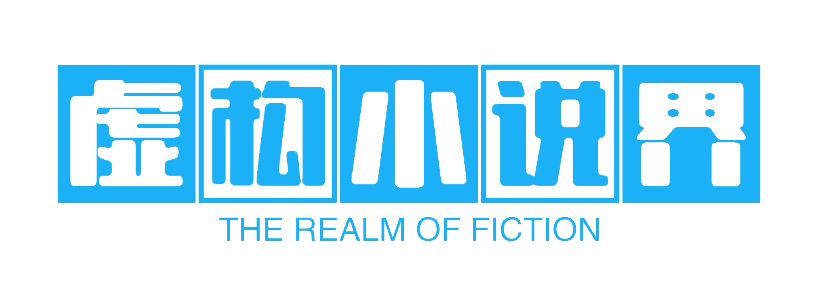第四十章
第四十章
蘇博士是個嘴硬的人。不遠不近的關系, 她該道謝道謝,該撒火撒火, 進退得宜。但是親近的人, 便有些羞于說感謝的話。這回她遭了事兒,徐宴所作所為她一清二楚。兼之昨日夜裡兩人胡鬧了大半夜,如今看徐宴, 蘇毓總是有那麼點兒不好意思的感覺。
徐宴從書房出來這會兒天色已經全黑了, 端坐在堂屋的主座上不知在想什麼,神情略有些戾氣。聽到腳步聲, 他擡頭看了一眼, 見蘇毓從屋外進來便起身站起來。
兩人四目相接, 蘇毓頓了一下。
将卷起來的袖子放下去, 她昂起下巴:“做好了菜, 你跟乘風去端。”
此時她立在門邊兒, 堂屋的燭火映照着她的面頰。
燈下觀美人,越看越美。徐宴的目光順着她的臉頰滑到她的脖子上,眸子暗沉下來。家裡沒有高清的鏡子, 蘇毓絲毫不知自己脖子上被印了不少紅印子, 尤其是後頸和耳朵後面這一塊。
他站着不動, 蘇毓飛快地眨了眨眼:“……怎麼了?”
“無事, ”徐宴收回視線, 勾起嘴角淡淡地笑了一下,一把抓住蹭着牆角嘴裡不知包了什麼東西的徐乘風小屁娃子, 單手拎起來便往竈下去, “開飯了, 我們去端菜上桌。”
蘇毓盯着他背影看了片刻,抓了抓頭發, 扭身進了卧房。
卧房裡頭的味道早就散了幹淨,髒了的被褥也拿出去洗了。蘇毓脫了燒飯穿的衣裳,剛要換一身,轉頭就看到床頭岸上擺的兩碟點心。一碟子豌豆黃,一碟子綠豆糕。她不大愛吃甜食,就這兩種點心會吃一兩塊。徐宴從外頭回來,還帶了這兩包小零嘴兒。
豌豆黃似乎被人動過,上面爪印還在呢。憶起剛才小屁娃子鼓着腮幫子蹭牆角往外跑的樣子,蘇毓忽然輕輕啧一聲,繃了一天稀奇古怪的心情莫名就松快了許多。
徐宴去到竈房揭了鍋蓋,見架子上四道葷菜。除了一道糖醋小排骨是徐乘風整日挂嘴邊要吃的,其餘全是他愛吃的,忍不住抿嘴一笑。
小屁娃子眼尖,巴在鍋邊一眼看到鍋裡的糖醋小排。他大驚小怪地哇地一聲,驚喜道:“糖醋小排骨!”
“嗯,”徐宴一巴掌拍掉他企圖去摸盤子的手。鍋蓋拿到一邊,親手将那盤小排骨端起來遞給他。看他拿穩了才笑道,“你端着去堂屋吧。”
小孩兒歡呼了一聲,端着小排骨歡歡喜喜地跑了。
蘇毓故意讨好,一頓晚膳自然是吃得父子倆都停不下筷子。徐宴吃相十分斯文,不曉得他到底從哪兒學來的用餐禮儀,一舉一動都透着一股别樣的好看。蘇毓其實也覺得自己現如今頗有點美色上腦,春曉一度以後失去理智。但知道也沒辦法,她這一雙眼珠子止不住地往徐宴身上貼過去。
徐宴眉眼不動,仿佛一無所知般不緊不慢地用着晚飯。筆直的背脊挺着,間或替夾不到菜的徐乘風夾幾筷子菜,眼睛是一眼都沒往蘇毓這邊瞥。
心裡告誡了幾聲一定要克制矜持,蘇毓癟了口氣,低頭好好用飯。
她低頭的一瞬,目不斜視的徐宴嘴角翹了翹。
慢吞吞地用完了晚膳,一家人放下碗筷,小屁娃子看到滿桌的碗碟心有戚戚:“……誰來洗碗啊?”
自從被他爹鍛煉過一兩回以後,五歲的小屁娃子切身體會到洗碗的苦,如今看到一桌的碗碟忍不住心裡發怵。他縮在桌子下面,特别小心翼翼地看了一眼他爹,又小心翼翼地瞅一眼他娘,生怕從這兩人嘴裡吐出讓他去洗碗的話來。
蘇毓擦了一下嘴,道:“你爹啊。”
徐宴看過來。
“我做飯,你洗碗,”一頓飯吃完又恢複常态的蘇毓理所當然道,“這不是應該的?”
徐宴:“……”
蘇毓微笑,雖然美色很上頭,但洗碗還是你來。
仔仔細細地刷了碗,徐宴一邊刷碗一邊忍不住又是笑。她悶聲不吭不說話的時候太疏淡,其實這樣也挺好,至少鮮活有煙火氣兒。
等收拾完了竈下,已經是戌時。
徐宴攜了一身水汽推門進屋,屋裡沒看到蘇毓的人影兒。他拎着煤油燈緩緩地走到桌邊,才看到床上的紗帳放下來。裡頭隐隐綽綽的影子在晃蕩,他走過去,擡手掀開了紗帳,吓得裡頭抹藥膏的蘇毓冷不丁一激靈。
徐宴筆直地立在床邊,一手還提着煤油燈,神情溫潤。入目就是蘇毓衣裳半解,手指挖了一朵藥膏正在臉頰微紅往下抹藥的模樣。
四目相對,氣氛有一瞬間的死寂。
一息之後,他驟然放下紗帳。偏過身子,許久,咳嗽了一聲:“……傷着了?”
蘇毓不知為何臉頰爆紅。她本身不是個害羞的性子。但自從跟徐宴略有些不清不楚以後,這厮的一舉一動,總是叫她面紅耳赤。
她嘴唇顫了顫,到嘴邊的話咽下去。手下快速地将藥膏抹好,蘇毓穿上了亵褲,沒好氣道:“傷沒傷着你不知道?這時候問我作甚?”
徐宴的臉低垂着,埋在陰影裡,昏暗的燭光下隻看得見通紅的耳尖兒。對于蘇毓的指責,他也不辯解,略顯僵硬地走到桌邊坐下,才緩緩道:“嗯,我知道。”
蘇毓:“……”特麼不如不回答,這樣回答她話都不曉得怎麼接下去。
又是一陣死寂,但空氣中彌漫着令人臉紅心跳的暧昧。
蘇毓迅速将身上疼得地方都擦了一遍藥膏,清涼的藥膏抹上去,破皮的疼就舒緩了。穿衣裳的時候蘇毓就忍不住吐槽,都是成年人搞這麼青澀真的沒問題?
直到衣裳全穿好,蘇毓掀了床帳下了床。
徐宴正在桌邊腰杆筆直地坐着。蘇毓從桌子邊繞過去,看到他手裡拿了一本書在看。
蘇毓:“……”有時候,她是真心地佩服徐宴這厮的意志力和自制力。她真的,甚少遇到一個像他這樣冷靜且克制的人。都這樣的場景了,他居然還看得進去書?不過也多虧了他淡定。見他如此冷靜,蘇毓剛才被人看到,心裡生出的那點古怪的别扭感就淡了。
她将藥膏放到妝奁裡,趿着鞋子走到梳妝台前坐下。
蘇毓背對着桌邊坐下,拿出裡頭買來的古代用的護膚品,一點一點的擦。徐宴眼睑才緩緩從書裡擡起頭。那一雙内勾外翹的眼睛擡了起來,眸中黑沉沉的。
年輕人精力旺盛,經不起激,這一點無可厚非。但徐宴心裡其實清楚,昨日得了那一回是有蘇毓被灌藥的影響在的。今日一大罐的清熱解毒的藥喝下去,床笫之事不大可能。再來,人受了傷,剛抹藥。無聲地吐出一口氣,徐宴低頭将書合上。
看半天一個字兒看不進去,不看也罷。
蘇毓慢吞吞地擦了臉,又抹了脖子和四肢,趿着鞋子又往床邊走。
徐宴這會兒已經不在桌邊坐着,人坐在床上。一條長腿自然地伸展,一條腿支着。一本書癱在他支起來的那條腿上,背靠着床柱在安靜地翻書。
蘇毓從床腳爬上去,越過他往床裡去。爬得過程中不小心蹭到他,兩人都是頓了一下。徐宴擡眼看了一下她,燈光照着他的半張臉,也看不清神情。除了一雙黑沉沉的眼睛,蘇毓頭皮一麻,麻溜地躺倒裡面去。等背對着徐宴睡好的時候她心裡忍不住就想抓頭發。
特麼他倆這到底是要搞個什麼鬼東西,演古代版的青春偶像劇麼?
蘇毓心裡糾結,但耐不住秒睡周公的召喚。隻幾息的功夫,她腦袋一歪又陷入了黑甜的夢境。
倒是床外拿着一本書看了許久的徐宴在聽到她呼吸平穩以後,一手蓋住了自己的眼睛。一張修長白皙的手遮着上半張臉,他低低地歎息了一聲,起身去了書房。
許久,等徐宴木着一張略顯酡紅的臉帶着一身水汽推門進來,他吹滅了燈,翻身躺下。
一夜無話。
次日醒來,又是一個陰雨天。金陵本就多雨的氣候,春夏多雨,被子衣裳常年都是潮膩膩的。日子一天天過去,陰雨綿綿的天氣隔三差五一回。
眼看着豫南書院開學的日子快到了,徐宴也要準備起入學的行李。
紙墨筆硯是肯定要帶的,讀書人不帶筆墨紙硯還讀什麼書?這不必說。徐宴收拾行李,主要是裝些換洗的衣物和梳洗的器皿。徐宴這厮别的都好養活,就一個潔癖很重。他用的器皿,平常是跟蘇毓徐乘風分開。家裡三口人,一人一套洗漱用的器皿。
蘇毓沒覺得他性子獨,反倒很欣賞徐家的這個習慣的。
事實上,在大曆的鄉下,物質條件匮乏,不講究的人家連洗漱都不洗,講究些的人家用的東西也都是一個盆一家人輪着用。徐家的這個習慣,蘇毓穿過來就很适應。
姑且不論這些,就說徐宴在收拾東西的時候,與蘇毓說了甄婉邀請兩人過府參宴的事兒。
蘇毓彼時正在替他歸類,聞言眉頭就一擡:“去柳家主母的壽宴?”
“嗯,”徐宴将衣裳規整地疊起來,隻見床榻上他衣服大小整齊得像遊标卡尺卡出來似的,他滿意地将衣裳一件一件放到箱子裡,“可以去一下。”
蘇毓聽着覺得他口氣古怪,意識到不對,便又問他:“可是出了什麼事兒?”
徐宴低頭整理,不緊不慢地又去拿了亵衣。本不想多少,但走了兩步,還是決定跟蘇毓明說:“孫老二的判令下了,孫家可能會找麻煩。”
蘇毓眉頭緊緊地蹙起來,心裡有種意料之中的果然。
徐宴收拾了一圈,又走到桌邊,仔細地将筆墨包起來。眼角餘光注意到蘇毓臉色凝重,又将手裡的東西放下去。他走到蘇毓身邊,拿走她手裡的幾本書,轉身塞箱子裡,淡淡道:“這些日子你在家裡待着,外頭的事情不用太擔心,總會有法子解決。”
擡起眼簾就看到徐宴一臉沉靜,仿佛毫不在意一般,絲毫不慌從容不迫。
蘇毓:“……”這厮也太沉得住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