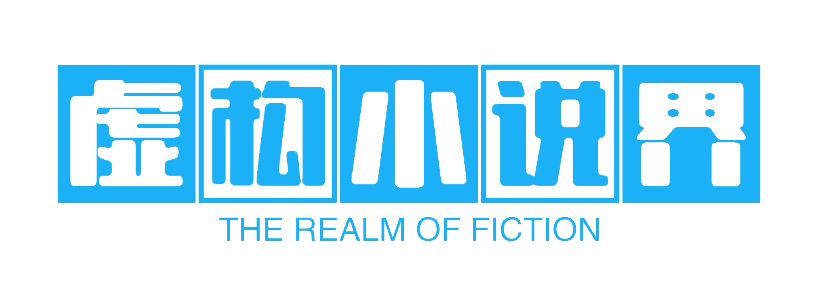她雖然文化水平低,見識少,可這個道理還是聽過的,奶奶給她說戲的時候聽了不少。
林婉晴張口結舌,真沒想到林蘇葉會這樣。
她怎麼敢,她怎麼敢管自己要東西!
剛才假模假式誇自己的表,原來在這裡等着她呢!
怪不得自己不寫時間她也無所謂,這是想訛自己的表呢!
她痛心疾首,“妹妹,這塊表是你姐夫給我買的,是他留給我的遺物啊……”
林蘇葉忙道:“哎呀,你别哭,我沒搶你的,我是說放在我這裡,我幫你保管,等過兩年你錢湊手了再贖回去,對吧?”
她一副非常大度、明事理的樣子,笑得人畜無害,溫文爾雅。
雖然穿着普通的農家衣服,發型也是普通的發型,可她生得美,這會兒突然就有了氣質。
林婉晴突然覺得嗓子眼裡有股子血腥氣,知道自己被氣得太厲害,太憋屈、太恥辱,咽不下這口氣,頂得慌。
她有些失去理智,怒火攻心,口不擇言道:“你想如何?讓我砸鍋賣鐵、賣血賣兒賣女還錢嗎?”
林蘇葉看着她,淡淡道:“堂姐,我壓着脾氣和你講道理呢,你想慢慢還,我同意,就算你很有錢,而我等錢用,我也不能逼你。你要是不肯留下手表,我看你這雙皮鞋也很好,你留着以後過來贖回。”
她起身把小姑穿着幹活的一雙布鞋拿過來丢在地上,雖然左腳拇指破了,右腳後跟有破洞,可林蘇葉還有點舍不得,“你可以先穿這雙回去。以後再來贖你這雙皮鞋。”
林婉晴的臉瞬間跟紙一樣白,随即又漲得紫紅。
她以為林蘇葉管她要手表就夠羞辱人的,沒想到還有這樣更羞辱的舉動。
她、她居然給自己一雙破鞋!
這是罵自己破鞋嗎?
簡直豈有此理,簡直是比直接扇巴掌還羞辱人。
她眼圈立刻紅了,身子晃了晃,忙扶着桌子。
林婉麗已經被林蘇葉的騷操作驚呆了,會還是林蘇葉會,狠還是鄉下潑婦狠。
沒文化就是無所畏懼,可以胡作非為!
林婉晴淚珠滾滾,咬破了唇,羞憤欲死,“妹妹,你怎麼、怎麼能這樣羞辱人!”
林蘇葉納悶地看着她,“怎麼啦?讓你放手表你不肯,那你還有其他值錢的當在我這裡嗎?”
她低頭看看,“這是我們小姑的鞋子。你腳比我大,穿我的肯定不行,穿小姑的可以啊。”
林婉麗就捏着嗓子提醒:“這鞋破了。”
林蘇葉罵她,“就你毛病多?破了怎麼啦?我們莊戶人誰能有雙囫囵鞋?天熱了我們還要穿草鞋,破鞋都是布的呢。”
她最讨厭有人用破鞋罵人,幹嘛欺負鞋子?
林婉晴卻不相信林蘇葉的解釋,覺得她就是羞辱自己。
她不能容忍被人這樣羞辱,再也顧不得肉疼舍不得,惡狠狠地把手表摘下來放在桌上,又賭氣般從兜裡拿出二十塊錢拍在桌上。
她紅着眼睛瞪林蘇葉:“你滿意了?”
林蘇葉歎了口氣,“你看,你怎麼弄得好像我是惡霸,強搶民女一樣?你欠我錢,用手表抵押,什麼時候有錢再贖回去,我也沒要你利息,你幹嘛老大不樂意的?”
林婉晴連連冷笑,在借條上寫清楚今天的日期,注明還二十元,抵押一塊梅花xx型号的手表,手表購于70年,價值310元。
她特意把70年寫得很用力,你看清楚,手表是70年買的,錢大部分是這之後借的,根本不是花你的錢!
林蘇葉湊過去看,念了念,型号的型之前沒機會用,也不認識,還很謙虛地指着問林婉晴:“這個字念什麼?”
林婉晴後槽牙咬得咯咯響,“你認識多少字?”
林蘇葉:“十來個吧。我們家人的名字我肯定都認識。”
林婉晴寫完,把筆摁在桌上,那架勢好像要把飯桌摁個窟窿出來。
她站起來,冷冷道:“不用送。”
她隻覺得頭重腳輕、天旋地轉,好像有什麼東西在自己腦子裡嗡嗡。
林蘇葉笑道:“那還是要送的。”
她把錢收起來,送林婉晴出去。
林婉晴雖然很生氣,卻還是秉承禮貌待人,跟薛老婆子告辭,死死地捏着自己的小皮包,踩着皮鞋咯噔咯噔地離開。
林婉麗朝林蘇葉露出一個又得意又幸災樂禍又複雜的表情,追着林婉晴跑了。
她們坐車來的,再去公社坐車。
出了薛家屯走上沒什麼人的小路,林婉晴一腔憋屈實在是無處發洩,趁着林婉麗不備,狠狠扇了她一巴掌。不扇一巴掌,她難解心頭之恨,她真的要憋屈死了。
林蘇葉太氣人了!
她一定要回軍區跟薛明翊說這事兒,讓薛明翊評評理。她男人死了,就算發了一筆撫恤金,可她還有兩個兒女要養,秦建民和别人都沒管她要錢,現在林蘇葉逼着她還錢,還扣押她的手表,這樣的婆娘他管不管!
她不是不還錢,她不是想賴賬,她想過兩年孩子大點就還,哪裡不對嗎?
林蘇葉幹嘛要這樣逼她?
她真是又屈辱又憋屈,感覺都要嘔血了。
林婉麗也懵了,撲上去就和林婉晴撕打:“誰怕你啊,裝什麼清高!”
姐妹倆就在小道上打起來,反正也沒人認識她們。
林婉晴:“你是不是故意坑我?”
林婉麗:“你要是心裡光明,不陰暗,你能來?”
林婉晴:“你惡毒!”
林婉麗:“你不惡毒?你打什麼算盤你當我不知道?沒關系,我愛連勝利,我就要纏着他一輩子,我樂意。”
林婉晴:“你會下地獄的!”
林婉麗:“你想勾搭别人男人,你下十八層地獄!”
林婉晴:“你污蔑我。”
林婉麗:“你沒惦記人家男人,你幹嘛不還錢!你怎麼不把錢都還給人家?”
林婉晴:“還說不是你寫的!”
林婉麗:“就是我寫的!就看不慣你個騷貨還裝清高樣兒!”
林婉麗雖然沒寫匿名信,隻要氣到林婉晴,能讓林婉晴倒黴吃癟,她簡直痛快得要成仙。
誰寫的她還要感謝對方!
恰好大軍小嶺幾個放學回來,路過那裡看到倆女人在那裡撕扯吵架,他們站成扇形仰頭圍觀。
吵架的兩人見狀忙分開。
林婉晴理了理頭發,扯了扯衣角,重新端起知識女性的架子。
林婉麗卻又煽風點火,“姐,你看那是大軍和小嶺,是薛明翊和林蘇葉的雙胞胎,漂亮吧。”
林婉晴微微揚起下巴,是挺好看,可自己的一雙兒女更好,懂事,長得也好看。
她還是主動和小哥倆打招呼,自我介紹是薛明翊部隊的戰友。
小嶺一聽是爸爸的戰友,立刻熱情起來,“阿姨,你和我爸一起打過仗嗎?”
林婉晴忙說沒有,男人打仗,女人不用的,她負責後勤工作。
大軍給小嶺糾正,“這叫軍人家屬,媽去了也是這樣。”
小嶺:“啊,原來不是解放軍啊。害我白激動。”
他對什麼表姨沒興趣,揮舞着彈弓吆喝着小夥伴兒們就往家沖。
大軍瞥了林婉晴一眼,兩人視線對上,都覺得不怎麼喜歡對方。
林婉晴覺得這孩子小小年紀眼神有些深沉,大軍覺得這表姨看着溫溫柔柔眼神有些刺。
都覺得對方不是好人!
等他們到家,發現媽和奶又在鬥嘴。
薛老婆子想和林蘇葉分那二十塊錢,被無情地拒絕,然後要五塊,依然被拒絕,最後一毛都沒撈着。
薛老婆子就吐槽她,“你說你,咋能拿雙破鞋換人家皮鞋?你這不是丢人嗎?”
林蘇葉:“她不是擱手表換了嗎?”
薛老婆子:“你以後對婉麗好點,她是來幫你的,我瞅着這閨女能處。”
林蘇葉:“你什麼都不知道别摻和。”
看給你能的,和林婉麗說什麼就站一夥兒了?
薛老婆子:“我有什麼不知道的?你不就是記恨人家嗎?當年你和那個妹夫相親,他眼瞎沒成?這都過去多少年,壇裡的鹹菜都爛成泥,孩子眼瞅着這麼大,你還計較那些事兒?”
小嶺一聽立刻豎起耳朵,哎呀,什麼相親,什麼男人,有戲聽!
後腳進來的大軍聽見奶的話,原本清冷的一張小俊臉就緊繃繃的,見小嶺一副看戲的模樣,就踹了他一腳。
小嶺捂着屁股:“幹嘛?”大軍乜斜他一眼,“白癡!”
小嶺:“哎呀,你想和我打架是吧。”他以為大軍挑釁他,想和他鬧着玩,就嗚嚎一聲蹿上去和大軍玩摔跤。
大軍不想理他,但是被硬纏着也隻能反擊。
莎莎就拍着小手喊油油。
林蘇葉沒顧得上打鬧的哥倆,怼薛老婆子,“你的好親戚之前來跟我說你兒子、我男人、孩子爹、薛明翊,在外頭有相好的。”
“噶?”薛老婆子沒聽清,她被林蘇葉那一堆稱呼繞暈了,“什麼相好的?”
那邊摔跤的哥倆也停下來,小嶺抱着大軍的腰,大軍用腿别着小嶺的腿,哥倆豎着耳朵偷聽。
薛明翊、有、什麼相好的?
林蘇葉硬邦邦的:“你和林婉麗嘀嘀咕咕沒問明白?”
薛老婆子:“放屁,不可能!我兒子什麼人我不知道?他打小就不愛和女孩子說話。也就你長得更好,要不他能要你?”
她和林婉麗可沒嘀咕這個。
林蘇葉看她又開始翻舊賬,就随便她念叨。
薛老婆子:“這麼說,你這倆堂姐堂妹都不是個好東西,以後别來往。”
一個說他兒子有相好的,一個欠那麼多錢不還還過來陰陽怪氣。
上一個跑家裡來陰陽怪氣的胡桂珠還在家“養胎”呢,你怕不是想和她湊一對兒。
她倒是沒責怪兒子借錢出去,就覺得薛明翊是個有分寸的,他既然借就肯定有借的理由。
林蘇葉:“我本來也沒來往,是你一次次熱臉貼上去。”她學着老婆子的腔調,“哎呀,他表姨來啦,進來坐,喝水不?過年好啊,家裡都好?工作好吧……”
薛老婆子聽她學得很像,就很沒面子,“我才不是假模假樣。你說你啊,長了張嫦娥的臉,非要配個王婆兒的嘴,不招人待見。”
村裡有個王婆兒,人稱二奶奶,是有名的神婆兒,雖然破四舊不能搞迷信活動,可她依然很有市場,畢竟鄉下大部分都沒文化,也沒有城裡那麼嚴格。
林蘇葉和婆婆相處久了,知道這是認輸的意思,便也休戰。
薛老婆子背着林蘇葉做個鬼臉,然後去拿柴禾準備做飯。
小嶺:“媽,什麼相好的?”
林蘇葉:“小孩子知道啥,别瞎打聽。”
小嶺就看大軍,讓大軍接招兒。
大軍冷着小臉兒,“不讓打聽,别當着孩子面兒說呀。”
林蘇葉聽得一怔,這孩子……以往大軍很少生氣,或者說懶得生氣,也不愛頂嘴,今兒這是不高興?
她一琢磨,聽着還真是自己不對,婆媳倆鬥嘴,不該當着孩子面兒。
鄉下人整天吵吵鬧鬧過日子,誰也沒考慮過不能當孩子面幹嘛,村裡孩子也對各家八卦了若指掌。
林蘇葉以前也沒那個意識,現在被大軍一說,她有點不好意思,下決心以後要改正。
大軍黑眸盯着她,眼神透着緊張,“所以呢?”
林蘇葉被他問住,不知道怎麼對付大兒子,就糊弄道:“什麼蓑衣鬥笠的,就是娘年輕時候相過好幾次親,你爹也相過,人都這樣。”
這是事實,也沒什麼好怕孩子的。
小嶺:“那你倆是相好的呀,為什麼說我爹外頭還有……”
“别胡說!”林蘇葉打斷他,“那是林婉麗瞎說的,你爹可沒。”
她好不容易讓父子親近些,可不能抹黑。
小嶺好糊弄,立刻就信了,“那yiyiwaowao真不是個玩意兒,以後别來咱家。”
大軍對林婉麗卻沒興趣,他問林蘇葉,“媽,那另外一個表姨呢?”
林蘇葉:“她呀,欠咱家一大筆錢,來還錢的。錢不夠,就把手表押給咱。我鎖在箱子裡,你們都不許動呀,以後要還給她的。”
大軍點點頭,他從來不亂翻林蘇葉的東西,隻有小嶺喜歡翻箱倒櫃。
他會看着不讓小嶺亂翻的。
林蘇葉讓他們寫作業,給莎莎準備了鉛筆本子繼續畫歪瓜爸爸,她則把小姑那雙布鞋刷刷,等幹了再補補。
雖然破了,扔是舍不得扔的,她尋思天氣暖和起來,不如直接把鞋面絞破,做成涼鞋,再繃上一圈布條就更結實。
她看小嶺滿頭大汗,頭發濕漉漉的,棉襖直接脫下來身上隻穿着件小背心,大軍卻還是棉襖扣得嚴嚴實實的。
她問大軍:“熱不?熱就脫下來換夾衣和坎肩吧。”
過了清明節就一天熱似一天,尤其今年節氣早,三月底就立夏,天氣就尤其熱。鄉下大部分人家布料短缺,一個人頂多兩身衣服,冬天絮棉花當棉衣,開春暖和起來等立夏就拆掉穿單衣,入秋涼了就兩件套起來。
隻有條件特别好的人家,才能冬天棉衣,春秋夾衣套坎肩,夏天單衣甚至短褲短袖。
林蘇葉家有薛明翊賺錢,還能拿到一些福利票,林蘇葉針線活兒又好,精打細算着分配就不用那麼緊張。
不過也是可着頭做帽子,每個人的衣服有數,沒得鋪張,能省則省。
薛明翊看着高冷嚴肅,可其實節儉得很,手巾用破的,部隊發的汗衫也穿到破。
林蘇葉用他的一個舊汗衫給小哥倆各改一件背心,穿在衣服裡面就很當事兒。
别看就一個汗衫,很多人家那是沒的。
大部分人頂多穿個褲衩子,外面就直接棉襖棉褲,根本沒有打底。
大冬天光身子穿棉襖,剛套上拔涼拔涼的,純粹用自己身體焐熱,等幹活兒出了汗,小風一吹,那冰涼冰涼的滋味兒,誰穿誰知道。
就城裡人很多都是毛衣或者棉襖裡面穿假領子,也不會真的穿一件襯衣。
人人限量供應布票,缺布啊!
眼瞅着小哥倆年後這三個月又長高一塊,脫下來的棉襖棉褲冬天就小了得重做,夏天的單褲褂子自然也小。
還得重做。
也是林蘇葉不肯給孩子穿得邋遢,别人家恨不得給孩子做個麻袋,從五歲穿到十歲的那種。她總是給孩子做得合身,闆闆正正,進城都不會被比下去的那種。
除了倆兒子,小姑也費布。
小姑力氣大,下地幹活那衣服褲子鞋子特别費,尤其肩膀、胳膊肘、屁股和膝蓋,隔三差五就得補,到最後就沒法補,總要換新的。
還要給小姑做夏天的單衣單褲。
她有錢可是沒布票,缺布啊!
林蘇葉手藝再好,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啊。
她有點犯愁。
林蘇葉問薛老婆子:“娘,我舅家不是自己織布來着?你去管他們買兩匹布來?”
薛老婆子娘家有兄弟姊妹,逢年過節也有來往,就她兄弟侄子還借她錢、票、糧都沒還呢。
雖然不是大筆借債,但是積少成多對莊戶人那也不少。
林蘇葉自小在大家族長大的,爺奶父母也是和親朋互通有無、互相幫襯的,所以她倒是也沒多自私不肯借人東西。
既然自己有需要,自然也該跟别人尋求幫助。
薛老婆子卻不肯,她抹不開面兒,人家都說她過好日子,她去借東西那不是讓人說兒子無能嗎?
人就是這樣,你有個風吹草動,别人就要說閑話。
今兒你胖了,他們說你是不是發财了?帶我們一個,不帶就是看不起窮親戚。
明兒你瘦了,他們說你是不是得絕症了?怎麼回事。
薛老婆子又沒見過别的世面,出來進去就是在村裡或者娘家,見的都是日常的親朋,身處其中自然被這種習慣裹挾,做不到不在意。
她道:“現在自家也沒地,撈不着種棉花,他們哪裡有棉紗織布?早多少年就沒的。實在不行,我去黑市淘換點布票。”
林蘇葉:“你可消停的吧,你是團長老娘,要是讓人抓了你說是批評你還是不批評你?”
薛老婆子:“那實在不行把我留着百年後的白布拿出來染染用。”
當地老人都有為自己準備壽衣和出殡白布的習慣,後來條件太差就攢不出來。
薛老婆子的是她婆婆當年連織帶買攢的,老婆子會攢家存了很多,百年後分給兩個兒子,薛老頭和薛老婆子也分到一些。
之前因為小嶺睡覺不老實,她和大軍沒法與之一個被窩,就拿出一部分做了兩條孩子的新子。
這會兒再拿也行,反正給孫子做衣服她舍得。
可它不合适啊。
那是厚的本色土棉布,做被子行,不适合夏天做衣服。
林蘇葉就盤算哪裡換點布票,隻是這年頭布票都按人頭發,普通人一年也就發個十五尺布票,誰家結婚、喪葬還得借,一般都沒有盈餘。
恰好楊翠花騎着自行車帶着一捆東西過來。
她把自行車停在門口,喊了一聲,“嫂子,在家吧,我是楊翠花。”
林蘇葉一聽,忙讓她進來。
楊翠花進了院子,随手把兩條日産化肥袋子卷着的瑕疵布放在地上。
她朝林蘇葉道:“嫂子,看這布中不中?”
林蘇葉樂了,真是瞌睡有人送枕頭,楊翠花這人真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