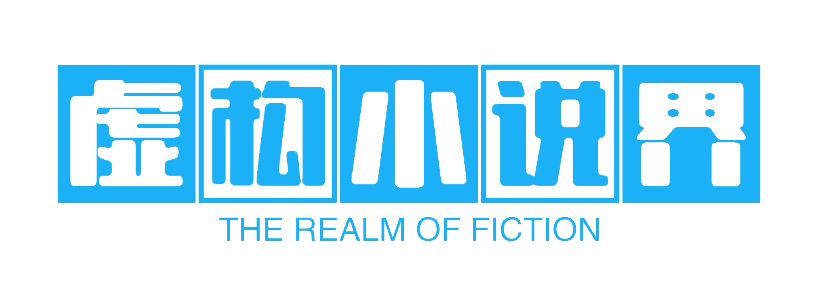人群中,牛車旁。
容溥看一眼王宮,一道深紅旗花,顯示丹野已經成功。
他笑着,手一擡,替寵姬接上了肩膀。
寵姬的手擡了起來。
容溥沒有給她武器,他不會授人以柄。
殺人這種事,想想辦法總是能做到的。
寵姬擡手,扯掉了嘴裡的血淋淋的布。
劇痛扭曲了她的臉,她的一隻眼睛已經被左司言給啃掉了,另一隻眼糊滿血沫,從腫脹的縫隙射出憎恨和憤怒的光。
左司言看見,不以為意,沙啞地笑一聲,一口唾沫呸在她臉上。
寵姬趁他這一偏頭,猛地咬住了他露出來的喉結。
她用盡了全部的力氣,牙齒尖而鋒利,狠狠地往死裡碾磨。
左司言沒想到她竟然會來這一手,手又擡不起來,拼命搖頭想要掙脫,可是強大的恨意讓寵姬絕不松口,越搖頭傷口越大血流越急。
他的親信副将本來不好意思多看這邊,也是害怕多看了會被大将秋後算賬,等到他發覺不對,左司言的血已經染紅了被褥。
副将大驚,一刀劈開了寵姬的眉心。
然而寵姬至死沒有松口。
等到副将好不容易把她的牙齒掰開的時候,看見的就是左司言咽喉上巨大的血洞,那鮮血如泉狂湧,看見的人一眼就明白這人絕沒有活路了。
左司言的親信将領都如遭雷擊,齊齊聚攏了來想要搶救。
此時已經到了王宮腳下,容溥看一眼王宮,帶着田武小武楊一休悄然走開。
深藏功與名。
站在王宮之巅的丹野,看一眼底下,忽然一躍而下。
跟在他身邊的大臣們一陣驚呼。
高興瘋了?
忽然一聲清亮的鷹唳,一道黑影如閃電橫劈而來,張開的雙翅從遠處看幾乎覆蓋了半個王宮金頂,那翅尖如利刃剖開這半山的雲霧,雲霧蕩開緩緩合攏,丹野和海東青交錯而過,手臂往海東青腳踝鋼環上一套。
海東青痛快地尖嘯一聲,帶着他穿雲掠霧,一層層越過宮阙。
最後在山底高大的宮門之上落腳。
王宮前左司言的軍隊,駭然擡頭看着那隻神駿的海東青。
那幾乎已經成為西戎傳說般的鳥,有着尋常海東青不能有的巨大身形,性能通靈,所向披靡。
而在它的身前,站着那個曾經的西戎少主。
丹野手一伸,抽出背後的弓箭。
他重弓重箭,一弓五箭,膂力無雙。
衆人才看見他手上出現弓,下一瞬空中黑光一閃,風雷之聲乍起,滿地的碎雪飏上半空,撲了人一臉。
耳邊隻聽得飒飒連聲,箭極速穿越空氣震動得耳膜嗡嗡作響,頭皮和頭發猛地一炸,渾身一涼,随即是沉悶的銳器入肉聲,沉重的物體倒地聲……
再睜眼時,就看見圍在大将身邊,他最看重的那些将領,已經橫七豎八倒了一地。
都是一箭穿心。
有的甚至還是一箭穿兩心。
隻一箭,就解決了所有最忠心于左司言的将領。
沒有勸降,不提迂回。
一絲生機和時間,都吝于給與。
衆人擡頭看站在宮門上頭那男人。
他拎着長弓,身邊伴鷹,凜凜如魔神。
一大隊人從他腳下的宮門中馳騁而出,伴随大聲呼喊:“左司言部下聽令!”
“左司言及部下諸将,罪在謀逆,現已伏法。着令查看家産,親眷流放翰裡罕漠。新王繼位,寬宏仁慈,前事不究,投誠者即授軍職,職滿不候!”
在西戎,軍職意味着家中會得到草場和自由,不會成為奴隸。而左司言當衆出醜,在軍士心目中地位本就一落千丈,能夠追随的将領又全部被殺,新王如此神勇引起他們的慕強心理,如今再将軍職如誘餌一般撒出,先到先得,衆人也就不再執着于陣營與忠誠,當即便有人抛下了武器,高喊:“我願為大王效力!”
“好!賞千旗之職!”
千旗是西戎軍中的中級軍官職務,帶領千人隊。
頓時無數人抛下武器,争先恐後效忠。
鐵慈也跟了下來,在宮門後人群中看着這一幕,欣慰一笑。
丹野在書院沒有白學,能駕馭好這些驕兵悍将,坐穩王位不在話下。
容溥走了過來,從懷裡掏出個東西給她,拉她到隐秘處,鐵慈打開一看,竟然是一張薄如蟬翼的人皮面具。
仔細看,是烏梁雲珠的。
鐵慈一瞬默然。
容溥道:“我總覺得烏梁雲珠吃的東西和裘無咎怕是有些關聯,這面具你先備用……”
聽他說到裘無咎,鐵慈心中一動,道:“至今還沒接到呼音大部隊的消息嗎?”
容溥搖頭。
“裘無咎的軍隊在哪裡?”
容溥一怔。
“呼音主力和裘無咎主力在對峙,呼音接到我們的消息之後就應該悄悄撤走,隻要她走得足夠快,裘無咎就算發現,也追不及。但是呼音主力遲遲沒到,是因為什麼耽擱了嗎?誰耽擱了她們?放眼四周,也隻有……”
“裘無咎。”
容溥皺起眉,這顯然不是什麼好兆頭。
鐵慈的目光四處梭巡,“剛才一片混亂,現在安靜下來了,我還發現一件事……”
“什……”
容溥的話還沒問完,就看見丹霜自上頭台階上奔下,邊跑邊揮手喊着什麼。
她本是和楊一休兩人去清點自己的隊伍,并收編投誠的軍隊,眼下顯然是發現了什麼要緊的事。
但此時鐵慈的目光落在了前方人頭濟濟的大街上。
大街上的士兵,仿佛也太多了些……
這麼想的時候,她忽然心中一動,随即眼前冷光一閃。
“下來!”
下一瞬她已經出現在宮門之上,一把抱住了丹野。
身後是來自好幾個方向的不斷旋轉放大的箭頭!
海東青憤怒的尖唳一聲,渾身羽毛炸起,猛地張開雙翅。
下一瞬鐵慈和丹野在它身後消失,無數碎羽在風中炸開,海東青一聲尖嘯,高飛而起,一頭紮向左司言軍隊所在的人群中心。
再下一瞬,鐵慈抓着丹野出現在宮門後,但随即趴在地上的她就聽見地面隆隆的震聲。
這聲音十分熟悉,她少時去軍隊視察,在狄一葦軍隊操練時也聽見過這聲音。
這是重型火炮被拉動時碾壓地面的聲響!
她一把抓起容溥和田武,對丹野大喊:“叫你的海東青一起回去!”
同時發力狂奔,把沖過來的丹霜撞了回去,丹霜跟她久了,立即腳跟一旋,回頭猛沖。
丹野此時也反應過來,一聲唿哨,示意海東青回轉。
就在此時,轟然一聲巨響。
偌大宮門在身後崩塌。
碎磚巨石砸在跑在最後的田武腳後跟,隻差毫厘。
鐵慈沒法帶多人瞬移,而且随着她其餘天賦之能的開啟,她能夠瞬移的次數也在減少。
海東青打着晃往回飛,半邊翅膀垂下,顯然是受了傷,丹野狂奔迎上,不顧危險跳起接住它,把它往肩膀上一扛,就一路狂奔。
一邊奔一邊喊,“下閘門!”
身後慘呼聲一片,在大街上的左司言士兵最先倒黴,不知道什麼時候,他們身後出現了黑壓壓的軍隊,軍隊包圍了整個王宮,鎖住了大街兩端,三門火炮被緩緩推了出來,靠近火炮的士兵被震死或者燙死,更多的是被後方來的箭殺死。
又是一聲巨響,但這回卻發生在長街上,火光沖天,無數人被沖上天空再砸落在地,這門炮鐵慈等人運氣很好,炸膛了。
火炮沉重難以攜帶,長途奔襲更容易讓其損壞,這裡能有三門已經是奇迹,鐵慈心裡明白,呼音那裡失利了,來的一定是裘無咎。
隻有裘無咎此刻才可能帶着攻城器械。
她制造了一場混亂,渾水摸魚獲得了勝利,同時也導緻西戎的王城被打開,進入了最虛弱的時期,這老奸巨猾的狐狸把握住了最好的時機,出現在了王宮之前。
他一定是先想法子解決了呼音的威脅,打散了她的主力,才可能這麼快地出現在王城。但是呼音的大營那麼隐蔽,又是怎麼被發現的?
無數的問題從腦海中一閃而過,她的腳步疾若星火,西戎的王宮形制特殊,依山而建,上山的石階盡頭轉彎處都有一座拱門,原本像是裝飾用的,此刻卻有很多士兵在指揮之下拉動拱門之側的一根鐵索。
鐵慈胸臆間忽然一堵,真氣流轉停滞,身形一頓。
丹野扛着海東青在她先一步進入拱門,回手來拉她,道:“快!快!”
拱門之前還有宮門的高牆擋住視線,拱門之後從第二層開始就暴露在大街的視野下,鐵慈讓開了丹野的手。在即将進入拱門之前,将容溥和田武往上一推,與此同時她取出那個薄薄的人皮面具,往臉上一抹。
丹野愣愣地看着她,不明白這個時候她在玩什麼把戲。
可等當鐵慈擡起頭來時,丹野的臉色就變了。
他眼前出現了烏梁雲珠。
随即他明白鐵慈是戴上了面具,此時也顧不上詢問,用目光焦急催促着。
容溥和田武已經進了拱門内,丹霜本來就在前面先進去了,衆人眼看大街上第三門炮緩緩移動,炮口已經鎖定了第一道山道上的所有人。
而那閘門已經落下一半,現在必須彎腰才能過。
卻在這關鍵時刻,鐵慈的速度慢了下來。
丹野十分驚訝,他算定鐵慈的速度沒問題才下令下閘,誰知道她怎麼忽然慢了?
鐵慈無法解釋。
因為她要做烏梁雲珠,烏梁雲珠武藝很平凡,她就必須符合人設。
她更不能展示天賦之能來對付這門炮。
裘無咎在軍隊裡看着,保不準他已經有了關于皇太女的猜測,她必須得隐身起來。
衆人瞠目看着她,不明白閃電豹怎麼忽然變成了兔子,眼看那炮就要轟來,還有那門就要合攏,性急的幾乎要沖回去。
門落下暫時就不能拉起,現在隻剩孩童高,丹野沖上去跪下,要用肩扛。
那閘門是特制,就是危急關頭用來抵禦萬軍的,他一個血肉之軀,如何能抗?
鐵慈早有準備,指間石子彈到丹野腳下,丹野滑倒,被他的人拉住。
鐵慈在這刹那回頭,屬于烏梁雲珠的臉眼神冒火看向大街。
身後轟然巨響,鐵慈一個猛撲,也似滑倒一般,在炮火來臨前一霎滑入門内。
長街上,也用千裡眼觀察着王宮山道上的一切的裘無咎,微微皺眉放下了千裡眼。
他方才沒有發現任何疑似皇太女的人。
他和塵吞天聯絡過,塵吞天說打敗他的人中有天賦之能特别強的人,他懷疑那是皇太女,可方才他也沒看見任何施展了天賦之能的人。
這讓他有點奇怪。
在這樣獲得勝利的時刻,皇太女沒有道理不在丹野身邊。
難道她還留在上面的大殿?
他又想起方才驚鴻一瞥的烏梁雲珠。
那小姑娘臉上白裡發青,眼下青黑尤其嚴重,顯然是吃了他的好藥了。
這讓他心中一動,仰望上頭的王宮。
他知道王宮的布局和設計并非出自西戎人之手,而是傳言裡的傳奇人物所做,那位除了武功之外,還有關于建築和機關的天賦之能,受西戎王族供奉,曾設計了王宮,王宮利用山勢建築,渾然一體,層層往上,每層縮進,最後一層離大街很遠,從第二層山道開始,山道之下便有各種機關埋伏,而山體也不可攀援,同樣有機關無數,每道閘門一夫當關萬夫莫開,簡直可以說是鋼鐵堡壘。
當初他沒有選擇立即進王城,而是隐藏野心,遠離王城,就是因為不想在王城王宮之下耗費太多的力量,将來被呼音丹野那些人所趁,回頭再被大王子打擊。
他集中力量将那些舊王族軍隊剪除,并給放松警惕的大王子他們送去上瘾藥物,等到舊王族軍隊滅掉,大王子那裡多少會有人中圈套,那時候他便有了可趁之機,可以輕松下王城。
如今被迫提早發動,他原本還擔心大王子那邊還沒放下戒心,應該沒人中毒,現在看來,他的運氣很好。
身邊将領知道他的計劃,由衷贊歎道:“大相算無遺策!”
贊歎發自肺腑,畢竟能在定安王身邊多年安然無恙,甚至還能在兩地發展出自己實力的人,他還從未見過。
裘無咎清瘦如老學究的臉微微露出笑意。
不,西戎隻是一處而已。
他目光投向南方大乾的方向。
這天下,何處不是他的棋局呢?
……
西戎王城風雲變幻,永平衛裡暗潮洶湧。
永平衛中最靠近大營的是牛頭嶺駐軍,駐軍三千人,帶兵的是衛将軍劉琛。
劉将軍最近傷了風,呆在營房裡寸步不出,連吃喝都是親信送進去。
天剛亮,有人來送熬好的藥,劉将軍親自來接,外頭忽然響起一陣馬蹄聲,有人大喝道:“樓指揮使及蕭副指揮使前來巡察,着令牛頭嶺駐軍準備迎接!”
劉琛關門的手頓了頓,把門一甩,探頭出去大喝道:“老子傷風還沒好,這些王八犢子能不能别一天騷擾三遍!”
他脾氣出名的不好,以前還和狄指揮使嗆過聲,來報信的士兵不敢和他裝樣,忙遠遠笑着安撫道:“上官要差,需要捉拿重犯,衛将軍包涵則個。”
“犯你親娘!”劉琛破口大罵,“你們要折騰随你們,到老子這裡來羅唣什麼?不曉得老子和那婆娘不對付?老子見了她,不說别的,先幹她一百遍!娘的,當初不就頂撞一句,竟然扒下老子褲子打。她要撞到老子手上,不用你們來搜,老子第一個先砍了腦袋!”
他說得殺氣騰騰,底下人聽了腦袋一縮,心裡倒也有幾分贊同。
原指揮使押送途中失蹤,永平衛上下翻了天,監軍和新任指揮使下令不計代價尋找,全軍都恨不得扒開鋪蓋查個幹淨,但要他說,就算别處要三番兩次清查,牛頭嶺最沒必要,一來離大營太近,狄指揮使腦子進水才藏這裡;二來牛頭嶺守将和大營最不合,和狄一葦關系最差,全軍都曉得,兩人對着拔刀都有過。
就因為關系太差,狄一葦才把劉琛壓在身邊,好就近方便罵他,全軍都知道這事。
誰藏狄一葦,這位也不可能藏啊。
但是最近軍中氣氛不好,監軍丢失了狄指揮使,火冒三丈,又不能确定指揮使到底跑哪了,有說她進京訴冤告禦狀去了,有說她潛伏回來等待時機報仇,還有說她已經死了。而又有消息說皇太女就在永平附近,聽說了狄指揮使的冤情,正在微服私訪,時機到了就要揭開身份為狄指揮使撐腰,再加上因為之前的事件,軍中士氣低落,怨氣極大,監軍和新任正副指揮使又要在進京道路上設卡,又要在全軍搜查,又要在附近村落中清理,又要查皇太女到底身在何方,用人還不怎麼順手,簡直是焦頭爛額,一團亂麻。
那傳令兵歎口氣,回去交差,不禁想起狄指揮使還在的時候,何至于如此!
這邊劉琛關上門,臉上暴怒的神情一變,讪讪轉過頭來。
房内軟榻上,半躺着一個人,長腿松散地伸着,見他轉頭,眉頭一揚,道:“來啊,來幹我一百遍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