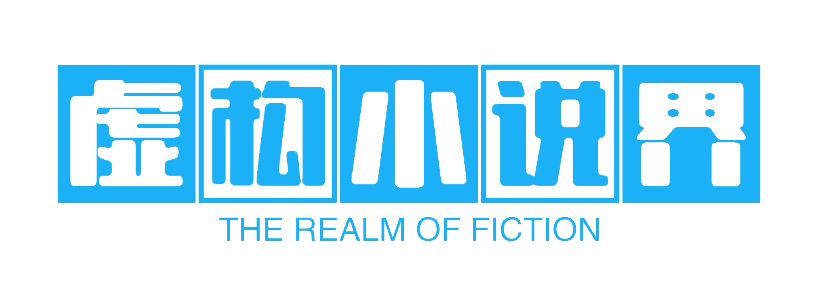楚霖在山坳裡和趙吉安說話,不知不覺耽擱了時間,他回來的時候,暮色正慢慢籠上來。杜家溝家家戶戶,屋頂都冒出了淡青色的炊煙,有做飯早的人家,已經飄出了飯菜的香味。所以在回來的路上,他并沒有遇見任何人。
杜櫻給許氏打下手做晚飯,杜梅在院裡洗衣服,見他進來,便很自然的接過他換下的衣服。
“梅子。”楚霖低喚。有一種不舍的情愫。
“嗯?”杜梅擡頭看他。她正想着趕在天黑前把衣服洗了,暗色裡并沒有注意他的異樣。
“沒事,我一會兒陪你去河邊,提燈照亮。”楚霖看看她白淨的臉,澄明的眼,想開口,卻又不知怎麼說,便岔到洗衣服上去了。
“過會兒讓杜桃給我照吧,晚上就不給你畫臉了。”杜梅埋頭洗衣服。
“好。”楚霖輕應了一聲,心裡卻是一片歎息。
這些時日,他漸漸習慣了杜梅每日給他畫臉,他坐着仰頭,杜梅很用心地給他描摹,盡量畫得和昨日一樣。她原說是給他畫個黑痣,結果卻畫成了胎記,他也由她。
每每淺淺的呼吸噴在他的臉上,溫暖地讓他酥麻,少女的甜馨沁入鼻端,世間恐怕找不出一種香料可與之媲美。他總是閉上眼享受這一時刻,隻願時間過得慢些再慢些。
“畫眉深淺入時無”,這比張敞畫眉也不差了,隻是差了最重要的一點,此時的他們,還是襄王有意神女無心。
“楚霖哥哥,你快來看,這是個啥?”杜桃和杜桂正在屋裡看《山海經》上的圖片,兩人争執不休,聽見院裡說話的聲音,忙找他評斷。
楚霖埋下心中念頭,進屋去和兩個小鬼頭說書。
天色完全暗下來,晚飯熱騰騰地上了桌,杜梅也提着着濕漉漉的衣服從河邊回來了。
“哎呀,我光顧着玩了,姐,你怎麼不叫我?”杜桃懊惱地跑出來幫忙擰衣服。
“今天月光好,我看得見。”杜梅笑。雖說入了春,今天東風刮得緊,河邊冷飕飕的,她不想妹妹們凍着。
四姐妹手腳麻利地晾了衣服,便上桌吃晚飯,今天許氏做的是南瓜粥,又甜又香。熱熱地喝了,杜梅才覺得周身的寒氣下去了些,連小腹的隐痛都好些了。
杜櫻搶着洗了碗,楚霖在屋裡給四姐妹講大順朝的名山大川,杜桂的眼皮子打架了,今天大家都太累了。
窗外的風肆意地撲打窗棂,夜裡怕是要下雨了。楚霖起身回雜物間,杜梅也出門去收衣服,她把在屋裡找出來的,父親以前留下的消腫藥膏遞給楚霖。
“這是……”楚霖不解地問。
“别逞強了,我知道你肩膀一定磨破了。”杜梅晚上看他肩膀一直不自然地聳着。
“你幫我塗下吧,我又看不見,白糟蹋了你的藥。”楚霖說得理所當然。
“等我收了衣服。”杜梅也不是第一次給他上藥,也不去想其他的。
半褪下外袍裡衣,杜梅看着兩邊又紅又腫的肩膀,心裡突然抽了一下,這人從前一定是養尊處優的,在這裡卻能忍着和她們一起
過苦日子。
杜梅用手指蘸着藥膏輕輕塗抹,她的手指冰涼,觸碰在他火辣辣的紅腫皮膚上,有一種奇異的舒适感。藥膏是清涼了,杜梅為了讓皮膚快速吸收,手指在他的肩頭來回摩挲。
“你還疼嗎?”杜梅問。
“疼!”為了貪念這一刻的美好,說個小謊也不打緊吧。
“梅子,我有名字的。”楚霖有點不滿。這女孩從來沒正經地叫過他,三個小的倒是把楚霖哥哥叫得賊溜。
“哦,那又怎樣?我還救了你呢,也沒見你成天把恩人兩字挂在嘴邊。”杜梅不以為然。
“你管杜樹叫哥,你也得叫我哥,每次叫我,你你你的,太沒禮貌!”說到這裡,楚霖不知怎的,心裡酸酸的,就攀比上杜樹了。
“樹哥和我一起吃我娘奶長大的,我叫他哥叫了十多年了,跟親哥哥似的。”杜梅說話間,換了隻手按摩,這男人細皮嫩肉的,這次被擔子壓得不輕。
“我還比你大五歲呢,總得叫我一聲吧。”楚霖誘惑道。
“叫你啥呀?”杜梅手上動作不停,随口說。
“你想叫啥都行。”楚霖有點小得意,誘騙成功。
“楚哥哥?霖哥哥?楚霖哥哥?”杜梅一身惡寒,這也太讓人受不了了。
楚霖正等着聽,沒想到,杜梅把好端端的美好稱呼叫得如同狼嚎,他頓時就洩了氣。
“你還是叫我三哥吧。”楚霖舉手投降。
“這個好,你在家排行老三啊?”杜梅偏頭問。
“嗯,你總可以叫我了吧。”不知道為什麼,楚霖今天偏執地想聽杜梅叫他,也許那個三日之約讓他心裡不安。
“三哥?三哥!三哥哥……”杜梅搖頭晃腦,促狹地把這三聲叫得抑揚頓挫,而聽在楚霖耳朵裡,竟是異樣地纏綿悱恻。
夜裡果真下了大雨,杜梅早在鴨棚裡辟出了一片地方,養着大白那十隻半大的鴨和幾隻雞,窗戶也用蘆席蒙着了。黑豹和黑妞卧在外屋。
第二日,雨勢不減,連下了一天一夜,鴨棚裡墊的草全濕了。
第三日,雨時大時密,下個不停,氣溫也跟着驟降。鴨棚裡新換了墊草,野菜和豬草已經用完。若光用糧食,百多隻鴨子一天就得吃掉平時五天的量。
杜梅穿上蓑衣想到田裡去挖野菜,被許氏死死拉住。這種天氣出了門就濕了,要是感染風寒,可就麻煩了。
減少了喂食,鴨子嘎嘎地叫個不停,杜梅急得在屋裡轉來轉去,窗外的雨絲毫沒有停下來的意思。
杜樹因為下雨,兩天沒有出工,聽到鴨叫聲,就到杜梅家來看看。
鴨子叫得揪心,一屋子娘幾個愁眉不展地坐在屋裡,楚霖怕降溫凍着鴨子,正在準備一個炭盆。
“還有什麼辦法呢?”杜樹聽她們說,鴨子斷了草料,也跟着着急想轍。
“咦,梅子,你不是說鴨子要放在河灘上養嘛,那河裡的水草能不能吃?”杜樹抓了半天頭,提出一個想法。他剛來的路上,看見河裡的水草長得像柳枝似的,飄飄蕩蕩。
杜樹的一句話,仿佛打開了一扇窗,令杜梅眼前一亮:“對啊,我怎麼沒想到!”
若是還拘泥于老傳統,喂的和村裡人一樣的鴨食,那她遲早要被這一百多張嘴吃得連骨頭渣子都不剩!
“以前從沒見人用水草喂過,能不能行啊?”許氏有點擔心。
“娘,養這百多隻鴨子,本就是冒險,現在也隻能試試,總不能眼看着鴨子餓得直叫。水草,魚吃得,鴨也能吃!”杜梅鐵了心。
“姨母,我陪梅子去!”楚霖換了身短打,方便幹活。
“嬸子,還有我。”杜樹不甘示弱地說。
“我們……”三個小的也躍躍欲試。
“你們在家!”杜梅不等她們說完,一口回絕了。
她們在家找出兩個筐,又拿了院裡三根晾衣服的竹竿,三人穿上蓑衣,帶上鬥笠出門,黑豹和黑妞率先沖進雨霧中。
這段時間雨水充沛,小河小壩裡的水都是滿滿當當的,水草長得碧綠肥美,在水中像美人的青絲般蕩漾。
起先三人各拿一根竹竿在水中攪,那些水草又滑又軟,看着纏在竹竿上,當提起來時,又全部滑落了。
“這可怎麼辦?”看得到,撈不到,杜樹抹了把臉上的雨水。
“梅子,把你的竹竿給我!”楚霖想起用筷子吃面條的時候。
他将兩根竹竿夾在腋下,兩頭伸入水中,朝那水草茂盛處繞動,然後往岸上用力拖拽,果然,糾纏在兩根竹竿上的水草,被撈上來不少。
杜梅高興地蹲在地上,把竹竿上的水草解下來,放在筐裡,杜樹見這樣做,立見成效,便小跑着回家找竹竿去了。
楚霖如法炮制,做得越來越順手,撈上來的也變多了。杜梅正蹲着把一捧水草放到筐裡,忽然,隻覺兩腿間一股熱流噴湧而出。
“自己憋不住小解了?”杜梅暗想,她被吓住了,一動不敢動。楚霖還在旁邊,她雖不拿他當外人,但畢竟男女有别。
楚霖見杜梅神情異樣,關切地問:“你怎麼了?”
“我沒事……啊……”杜梅的話還沒說話,又一股熱流湧出,她的小腹如刀攪般疼痛,疼得她腰膝酸軟,差點栽倒。
發現杜梅臉色迅速慘白,楚霖心知不妙,忙扔下竹竿,一把扶住她的腰,觸手處一片熱的黏~膩。
“我是不是要死了?”發現異樣的楚霖把手伸到眼前一看,杜梅同時也看見了他滿手的血。
“你哪裡不舒服!”楚霖被吓到了。黑豹和黑妞也被血迹刺激到了,都大叫起來。
燕王府裡,除了如意,其他的丫鬟婆子,在他眼裡和男仆沒什麼兩樣,多一眼也不會看的,而如意呈現在他面前的,永遠都是最完美的一面。
“我肚子疼,像要撕裂了一樣,我是不是要死了?”饒是杜梅大膽,此時的她,也被吓得緊緊抓住楚霖的衣襟。
她不想死啊,她娘和弟妹還靠她養活呢,家裡那百多隻鴨子,她還想好好大幹一番呢,怎麼能就這麼死了!她不甘心!2k閱讀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