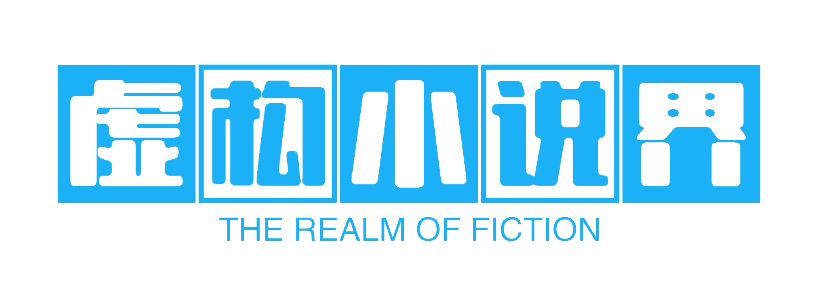“沒事,你不會有事的!我也不會讓你有事的!”看着杜梅虛弱的樣子,楚霖心疼得厲害,比自己受傷還要疼。
“三哥,你答應我,如果我死了,你一定要照顧我娘和弟妹們!”杜梅哭了,不僅是身體難忍的疼,還有内心絕望的痛。
“我才不會管,你自個好好活,自己管!”楚霖聽不下這傷心話,見杜梅滿臉淚痕,也顧不得規矩綱常,一把打橫抱起她,這女孩太輕,抱在手上,輕得如同一片羽毛,他将她窩在自己懷裡護好,腳步如飛地往家中趕去。
雨下得更加猛烈,打在臉上又冰又疼,黑豹和黑妞像離弦的箭,沖破雨簾,在他們前面狂奔。
“除了你,我沒有其他人可以托付,我要你答應!”杜梅疼得五内如焚,痛不欲生,不免使了小性子,緊緊揪着楚霖衣襟說。
可憐她,欲将一家子弱幼托付給一個陌生人。自家爺奶不待見她們孤兒寡母,大伯母和三嬸更是恨不得二房立時絕了戶,好瓜分他們的田地。
杜鐘和杜樹固然對她們好,但他們父子自己時常揭不開鍋。再說,他們一家是男人,她們一家都是女眷,這哪怕站着多說一句話,都會招來是非,又何談托付?
“我管,我管還不行嗎?咱們回家,我立刻去請鐘大夫!”楚霖心亂了,胡亂地答應。他還沒跑到院門口,黑豹黑妞就已齊聲狂吠。
許氏趕來開門,就見楚霖抱着面上失了血色的杜梅闖了進來。她心中一亂,腳下差點滑倒。
踉踉跄跄的許氏跑回屋裡,就見兩個水人站在屋裡,滴滴答答直往下淌水。三個小的,正手忙腳亂地把床鋪展開。
“這是出什麼事了?”許氏顫着聲問。
“娘,我肚子疼,還流血了,我是不是要死了?”杜梅弓着身子,摁着肚子,畢竟是個十來歲的女孩子,見了娘,又委屈又害怕地哭了。
許氏一見杜梅裙子上的血迹,心下了然,神情也緩和了下來。
“梅子,别怕,不會死人的,這是正常的,你長大了。”許氏和顔悅色地安慰杜梅。
她轉身對杜櫻說:“快去打熱水,給你姐洗洗。”
許氏語調平緩,安撫了杜梅緊張的情緒,但她不明白,自己已經14歲了,自然早就長大了,可母親說的長大為什麼要這麼疼!
楚霖模模糊糊似乎明白了點什麼,具體是什麼,他也不清楚。總之,杜梅這是沒有生命之憂了。
見這情形,他也不便待在家裡,就還去河邊撈水草,等他和杜樹将兩大筐水草弄回家的時候,杜梅已經收拾幹淨,睡下了。
許氏煮了熱熱的姜茶,給楚霖和杜樹每人喝了一大碗。雨太大了,楚霖隻好在雜物間簡單擦洗,換上幹的衣服。
杜櫻将水草切碎,試着喂了點,饑餓的鴨子也不挑食,一會兒就搶吃完了。
杜梅睡得連晚飯也沒有起來吃,她聽了母親說的話,羞得滿面通紅。這會兒睡着了,倒是免了與楚霖見面的尴尬。
夜裡雨漸漸小了,天光将夜色一點點暈染,仿佛一滴水将濃墨化開。
“嗚嗚,爹……爹,你别走,梅子怕!”一聲帶着哭腔的
呓語。
“姐,你怎麼了?”挨着杜梅睡的杜櫻,發現她的身子滾燙。
“你姐發燒了!”許氏披着衣服,下床查看。
“這可怎麼辦?”杜櫻急了,大姐從來都是她們一家依靠的堅實肩膀,這個時候卻脆弱得像個布娃娃。
楚霖睡覺一向警醒,心裡又惦記杜梅,他聽見裡屋的動靜,便穿衣起來詢問。
“姨母,出什麼事了?”楚霖扣門。
“梅子昨日着涼了,有點發燒。”許氏隔着門說。
“要不要緊?”本以為昨天鬧了個烏龍,現在卻是真的病倒了。
“家裡有些草藥,我馬上熬點給她喝。”許氏穿好了衣裳,打開了門。
楚霖隔着門,朝裡望望,三個小的都起了,把床騰給杜梅一個人,讓她睡得舒服點。
草藥在爐子上咕噜咕噜冒着煙,院裡地上一片泥濘,楚霖便在雜物間練了會兒功。
躲了三天的太陽,終于欲語還羞地出來冒了冒。鴨窩裡撤了炭盆,換上幹草,鴨子們似乎更喜歡水草的滋味,吃得幹幹淨淨。
許氏喂了杜梅藥,她意識有點清醒,倒惦記着楚霖的胎記,強撐着幫他畫了。又重又粗的呼吸,滾燙的指尖,楚霖不舍得她如此辛苦,潦草畫畫便罷了。
今天是楚霖與趙吉安約好回去的日子,可杜梅這樣,他實在不放心走。他悶悶地埋頭幹活,挑水,劈柴一刻也不讓自己歇下來。
吃了午飯,杜梅依然不見好轉,病情越發沉重起來,臉上燒得跟火炭似的,叫着也不應。許氏伸手摸了下被子裡,一片濡濕,她的臉色瞬時煞白。
“楚霖,你趕快去鎮上請鐘大夫!”許氏急急地出來說。
“啊,好!”楚霖丢下斧子,來不及問,一陣風似出去了。
陰雨綿綿,乍暖還寒的天氣,生病的人挺多的,餘濟堂門前排滿了病患。
“鐘大夫在哪?”楚霖一下子撲在櫃台上。
他臉上的胎記本就吓人,加上他着急的神情,愈加顯得猙獰。
“鐘大夫在裡間坐診呢。你誰啊?”櫃上的夥計不認識他,避後幾步問。
“我……我妹妹得了急病!”楚霖不知道怎麼對外人說他們的關系,隻好含混過去。
“這都是得急症的,鐘大夫忙得很,個個都要上門,哪裡忙得過來?”夥計公事公辦地說。
閻王好見小鬼難纏,楚霖也不和夥計廢話,直接就往裡間闖。
“嗳,你這人,看病要排隊!”門口的夥計伸手攔他。
楚霖輕巧一個轉身,便閃進了屋裡。鐘毓正在給一個大爺開藥,擡頭一見他,愣了下,對嘟嘟囔囔想上來趕人的夥計揮了揮手。
大爺拿着藥方出去了,門口的夥計也識相地把門關上出去了。
“你怎麼來了?”鐘毓在十裡八鄉出診,他不要開口問,就把杜梅家的事聽了一耳朵。楚霖的胎記再可怕,鐘毓是見過真容的,一眼便将他認了出來。
“梅子病了!”楚霖上前一把扯住鐘毓的袖子,就要拖走。
“梅子身體一直很好,她怎麼會病?”鐘毓疑惑地看着楚霖。
楚霖便把昨日鴨子斷食,出去撈水草的事說了。連帶着還說了杜梅的血和“傷”。
“淨胡鬧!這是要坐下病的!”鐘毓一臉氣憤地拍了下桌子,對着楚霖發了一通脾氣。
他管不了外面的病患,立時收拾了藥箱。和外面的夥計交代了幾句,急匆匆地帶着楚霖從後門出去,駕了馬車就往杜家溝趕。
三個小的,從來沒見過杜梅生病,三雙眼睛悲悲切切地盯着她看。許氏買了瓶燒酒,給杜梅全身擦拭降溫。
黑豹不知哪去了,黑妞一天都沒見到杜梅,有點無精打采地卧在院子裡,它一見鐘毓進來,立刻跳起來大叫。
杜櫻聽到聲音,出來瞧見鐘毓,仿佛見了救星,趕忙上前一把抱住黑妞。
鐘毓幾步便跨進了屋子,許氏并沒有避開,屋裡本就逼仄,再說,杜梅這種狀況,她也不放心出去。
鐘毓二話不說,上前把脈行針,技藝娴熟,手法老道,接着又喂下一粒藥丸。他在桌上鋪開紙,凝眉刷刷地寫藥方。
“鐘大夫,我家梅子怎麼樣?”許氏小心翼翼地問。
“怎麼能這麼不小心,未婚女孩子月事最是要緊,昨兒那種天氣,怎麼能讓她淋雨!”鐘毓氣惱地說。
“梅子還是第一次來。”許氏低頭愧疚地說。
鐘毓也覺得話說重了,剛才光着急梅子的病,也沒仔細考量許氏的心情。
“抱歉,是我唐突了。”鐘毓站起來緻歉。
他怔怔地看着面前的婦人,三十多歲,身形瘦削,面色很白,仿佛看得見皮膚下細小的血管,生活的重壓和内心的隐忍,讓她原本一雙好看的眼睛,微微低垂着。
他認得她,依稀還是原來的模樣,可她卻認不出,面前的鐘毓是誰。十六年過去了,當年的一個青澀少年,早已長成如樹般挺拔的成熟男人。
十多年前,她救過他,一個多月前,他來救過她和她的孩子,如今,他又來救她的女兒,他與她,真的隻能循環這種救與被救嗎?
“鐘大夫,鐘大夫……”許氏見他出神,忙喚他。
“啊,我把藥方開好,讓他跟我去取藥吧。”鐘毓回過神來,忙掩飾地坐下來繼續寫藥方。
為了節約時間,楚霖是車夫趕着鐘毓的馬車送回來的。
鐘毓的醫術果然名不虛傳,紮針吃藥,又喝了一副湯藥,血止住了些,杜梅也慢慢睜開了眼睛,隻是身體還是虛弱,軟綿綿的。
許氏摸摸她的額頭,熱下去了些,沒那麼燙了。
楚霖不方便進去,他在門口朝杜桂使眼色。在這家裡,杜桂最是崇拜他,喜歡他講《山海經》裡的奇鳥怪獸,更喜歡他講外面天地的風土人情。
“你姐怎麼樣了?”楚霖彎腰問出來的杜桂。
“大姐好點了,娘說退燒了。”杜桂哭過,聲音啞啞地說。
“哦,這便是了。”楚霖懸着的心放了下來。
“進去吧,陪着你姐,有事來告訴我。”楚霖摸摸杜桂的腦袋。
“吱呀”一聲,院門響了,黑豹進來了,後面跟着一個黑色的身影。2k閱讀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