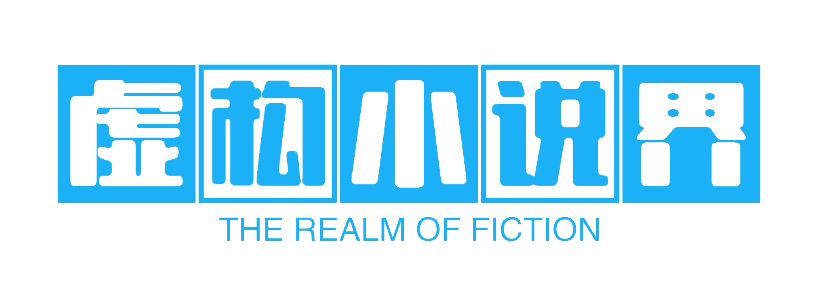“東家,活我都做完了,天太悶熱,原隻想在這歇會兒,不覺耽誤了。”馬榮面有羞色,趕忙解釋。
“好啦,姐也沒怪你,吃飯吧。”謝氏蹲下,将食盒打開。
馬榮還等着謝氏罵他,到時惱羞成怒把他趕走更好。沒成想,她居然這樣對他,馬榮摸摸鼻子,頗覺無趣。
馬榮盤腿坐下吃飯,謝氏半跪在他對面陪着,給他搛菜。他一擡頭就看見抹胸襦裙露出的大片雪白肌膚,這讓他煩躁不安,更令他生氣的是,他的身體起了令人羞恥的變化。
他埋下眼眸,食不知味地草草吃了飯:“東家,眼看要下雨了,你回去吧,田裡還有些雜草,我再拔拔。”
“雨來還早呢,你拔吧,我等你,這會子起風了,田裡比家裡還涼快呢。”謝氏不以為意,她迎風眯了眯眼睛,将鬓發抿到耳後。
她是過來人,早看出馬榮的異樣。今日天公作美,原在田裡勞作的鄉人怕下雨,紛紛回家了。天時地利,她隻等他屈服,做她的裙下之臣。
馬榮尴尬了,他坐着尚能遮掩,若站起來必然露餡,他不想被這女人看了笑話去,借機挑逗他。
“飯前無力飯後癡,我先小睡會兒,等會兒再拔。”他索性躺倒屈膝,翻身朝裡假寐。
“呵呵,你睡吧,我給你攆蚊子蒼蠅。”謝氏半窩在他旁邊,拿帕子在他臉上揮來揮去,馬榮佯裝不理。
謝氏膽子愈發大了,腰身慢慢挨着馬榮的後背,帕子不知拿什麼香料熏的,一股奇異的味道。
帕子似有若無的觸碰到他的臉上,此時此刻,馬榮的感官異常敏感,帕子雖輕若羽毛,卻偏偏像一把重錘錘擊他的心髒,他的呼吸漸漸變得粗重起來。
“咔嚓嚓”一道閃電撕裂暗沉的天空,随之“轟隆隆”的雷聲從天際滾過。
馬榮再不能裝睡,他一骨碌爬坐起來,謝氏順勢滾入他的懷裡,嬌嗔道:“我怕!我好怕啊!”
四目相對,謝氏媚眼如絲,勾魂攝魄,馬榮卻是雙目赤紅,如狼一般!
瓢潑大雨傾倒而下,兩人衣裳瞬間盡濕,仿佛這天下的不是雨,而是點着了的油!馬榮最後的理智和恥辱被欲念燃燒殆盡,他猛然發出野獸般的吼叫,将謝氏一裹,一個翻身,雙雙滾到茅草堆裡去了。
以天為蓋,以地為床,串珠雨簾做幔,漫天茅草成褥,這兩人瘋了。
“你這個婊子,賤貨!”男人的語氣中難掩厭惡。
“我賤,你不就喜歡這樣的嘛!”女人嬌笑連連。
……
咔擦擦的白練,轟隆隆的雷鳴,天地渾然一色,黑得伸手不見五指。雨下得急切而猛烈,試圖沖刷野地裡的醜陋和肮髒。
人沒有前後眼,也不是先知,預見不了将來。謝氏此時還想不到,不久的将來,馬榮,這個她以為可以玩弄在手掌心的長工,會毀了她的家,改了她的命!這,當然是後話了。
六月天,孩兒面。昨兒下了一夜傾盆大雨,今早依舊是紅豔豔的太陽當頭照。路上泥濘不堪,得虧有了牛車,杜梅可以拉着吃食照常去集市上賣。
杜梅還沒做幾筆生意,就見春芽急急地來了。
“他呢,他呢。”春芽一見杜梅,就着急忙慌地拉着她,指着老頭的攤子問。
“今兒路上不好走,他大概不來了。”杜梅看着春芽,路上泥濘難行,她的裙子上濺得滿是泥點,一雙鞋更似泡在泥漿裡,完全看不出花色來。膝蓋上還有兩團泥印,恐怕是在路上摔倒了。
“不會的,我等等他,他就來了。”春芽有些失望,但更抱着莫大的希望。
今兒春芽既不喝如意湯,也不吃茴香豆,隻搬張小凳子坐在門口,眼睛一瞬不瞬地看着對面的攤子。
她癡癡地坐着,來吃湯的人難免多看她幾眼,多嘴長舌的又要打聽議論一番。
過了半晌,春花秋果氣喘籲籲地來了。
“我就說她到這兒來了。”春花一指梅記食鋪門前坐着的春芽。
“真是一不留神,老母雞變鴨!”秋果小大人似地歎了口氣。
“累死我了!”兩人進了攤子,直接一屁股坐在門檻上。
“昨兒送回家不是好好的嘛,這是咋了?”杜梅小聲問道,并朝春芽的背影努努嘴。
“别提了,她一覺睡醒,發現身邊隻有我們,鬧着找老頭,直折騰了半夜,藥也不肯吃,我們隻好哄她今天來找他,才勉強吃了藥。”春花接過大丫倒的水咕隆咕隆喝了大半。
“我今兒隻說了句,吃了早飯再走,她就沒影了,吓得我們連走帶跑趕來找。”秋果接過杯子,毫不客氣的将剩下的水喝了個底朝天,仍不解渴,又讓大丫倒了半杯一氣灌了下去。
“這可如何是好呢!”春花緩過來,歎息道。
“俗話說,病來如山倒,病去如抽絲。她這病生得古怪,恐怕不是一時半會就能拔根去竈的。”杜梅細細安慰道。
“理是這個理,可若是春芽姐這般發花癡,不要說再找什麼婆家了,就是我大伯父一家都活的沒了顔面,肯定被唾沫星子淹死了!”春花絞着手指,低聲說。
“你今天抓藥嗎?過會兒我跟你一起去,再問問舅舅。”杜梅思索道。
“嗯,大伯給我藥錢了,他還說要謝謝你呢。”春花朝杜梅擠出一個笑臉。
天氣熱了,光坐着都出汗,來吃熱食的人少了,杜梅雖減了量,但還有一些沒賣掉。她瞧着時辰不早了,就把攤子交給大丫和杜桂,她和春花去醫館找鐘毓,留秋果看着春芽。
昨兒大雨,老人孩子生病的不少,鐘毓忙得焦頭爛額。他一見杜梅來了,剛好抓她當差,他口述,讓她幫着寫藥方。
春芽的藥,配伍的藥材比較多,鐘毓斟酌了方子,讓春花先去抓藥。
“鐘大夫,快給看看我兒子吧。”一個肥碩的婦人抱着個四五歲病歪歪的瘦小男孩,焦急地說。
“你這孩子發熱了,昨天淋雨了?平時是不是不愛吃飯?”鐘毓把了脈,看了舌苔和眼珠後問道。
“對呀,鐘大夫,你說的一點不假,都是他爹不是東西,非給他吃些亂七八糟的!”胖婦人氣哼哼地說。
“他都給小孩吃什麼了?”鐘毓擡
眼問。
“沒一樣正經東西,糕點,蜜餞,糖果,有次還想給他吃老山參,幸虧被我娘攔下了。”胖婦人絮叨叨地說。
“這些萬萬不可給小孩兒吃太多,他的脾胃虛弱,克化不了。”鐘毓叮囑。
“你這死泥鳅還不進來!聽聽人鐘大夫是怎麼說的!”胖婦人朝外面吼了一嗓子。
一聽這話,鐘毓和杜梅相互看了一眼。
“我聽着呢,聽着呢,你瞧看病的人這麼多,我又擠不進去。”果然是黑蛟龍,他陪笑地出現在門口。
胖婦人一手夾着孩子,一手擰了黑蛟龍的耳朵,直接提溜到鐘毓面前。
“咳,小孩子還是以吃飯為主,注意葷素搭配,可以适當喝些牛乳羊奶之類的,其他的能免就免。”鐘毓握拳假咳了一聲,掩蓋臉上的笑容。
“是是是,我記下了。”黑蛟龍一臉謙卑地說。
“今日先開去熱的方子,梅子,我來說,你來寫。”鐘毓輕叩了下桌面。慢慢說出各種藥名。
“那不吃飯咋治?”黑蛟龍如獲至寶,吹着墨迹未幹的紙,焦急地問道。
“所謂是藥三分毒。你先給他戒了零嘴,好生米飯養着,若還不行,再來開藥。”鐘毓看了看胖婦人手裡的孩子。
“謝謝!謝謝鐘大夫!”黑蛟龍一家退出去取藥。
一直看診到巳時五刻,外面病患都沒人了,鐘毓這才得空喝了口茶。
“今兒得風寒的人還真不少。”杜梅擱下筆,站起來搖了搖胳膊,晃晃腦袋。
“嗯,你回去多想想,為什麼同是風寒,我開的方子卻不盡相同?”鐘毓對杜梅真的是傾盡所學認真地教,卻又不是強行灌輸,而是将讀書和實踐兩者很好的結合起來,更有直觀的感受。
“好,我細細琢磨下。”鐘毓問的問題,正是杜梅想不通的,既然舅舅要她自己悟,她便要好好想想。
“春芽今天又來找老頭了,她可怎麼辦呢?”春花和秋果抓了藥,蹑手蹑腳進來,苦惱地問。
“她來找老頭,不過是他在危急的時候救過她,對他比較信任罷了。她時而清楚,時而糊塗,把他當依靠也是有的。”鐘毓聽了她們的話,分析道。
“可這外人不明了啊,流言殺人呢。”春花皺眉道。
“她這病宜疏不宜堵,還是要抓緊治。”鐘毓也不好怎麼說,這世上,女孩子的名節比性命還重要。
眼見着時間不早了,杜梅與春花姐妹向鐘毓告辭而去。
回到攤子上,大丫和杜桂已經收拾好了,搬上了馬車。秋果正苦口婆心地勸春芽,春花一見如此,心裡焦急如火,難免聲調變高了。
可偏偏春芽油鹽不進,說什麼也不肯跟她們走,非要在集市上等老頭。
杜梅心裡直犯嘀咕,老頭平素不是個躲懶的人,為啥好端端放着生意不做了?難道真的為了避嫌?
“春芽,你跟我回杜家溝吧,我們到他家裡尋他去,好不好?”杜梅想不明白,決定還是上門去看一下。2k閱讀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