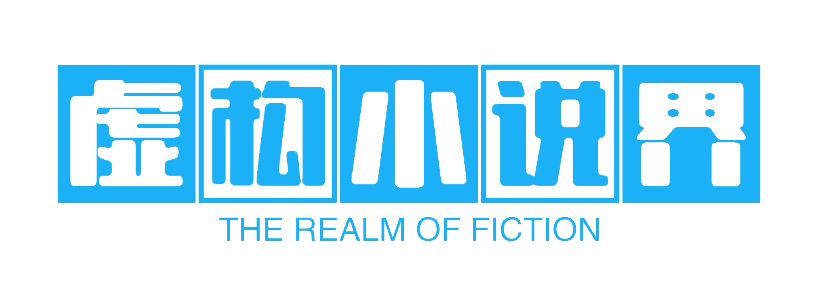“我可沒有多餘的銀子了。”杜梅困惱地說。
“傻丫頭,誰要你的銀子!我隻要這個。”鳳仙點點杜梅的額頭,伸手将福豬抱在手中。
“這恐怕做不了,我和葉丹簽過契約的,唱賣的玩偶隻能是獨一無二的。”杜梅堅決地搖搖頭。
“我又不要一模一樣的,隻是想要個小的,豬寶寶。”鳳仙手裡比劃着,說着說着,臉上泛起了紅暈。
“這……”杜梅沒想到鳳仙想要這個,如此想來,她多麼期盼有個孩子啊。
“契約裡肯定沒寫這個吧?”鳳仙一臉渴望地看着杜梅。
“你是想要個男~寶,還是女~寶?”杜梅看着鳳仙眼中的期許,實在不忍心拒絕。
“這個……我若說兩個都想要,你是不是會說我貪心?”鳳仙托着下巴愁眉苦臉地說。
“契約上雖沒明說,但總是逾矩了,我私下裡送你個女~寶吧。”杜梅硬着頭皮說,不知道葉丹知道了,會不會怪自己。
“爺最喜歡女娃娃,這下,他倒稱了心如了意。”鳳仙伸手扭了下福豬的耳朵。
“我剛看姐姐在繡絲帕,若你願意,我也可以教你的。”杜梅看鳳仙似乎更想要男~寶,便想着教會她。
“我那個女紅,哪裡拿得出手!一年半載繡不出個絲帕香囊之類。”鳳仙羞赧地低垂下頭,露出一截雪頸。
鳳仙在長大,老鸨見她日漸出落的标緻,有意把她栽培成搖錢樹。琴棋書畫,詩詞歌賦都請人專門教授的,偏女兒家的針黹女紅是青樓楚館最用不上的功夫,所以,鳳仙對此一竅不通。
她日常的衣裳裙裾都是外頭成衣店買的,零頭零腦的小件都由她的丫鬟小蓮一手操持。宋少淮贖了她,順便也贖了小蓮,如今困在府中時日多,鳳仙閑來無事,便跟她學繡絲帕。隻這幾日小蓮家裡母親病重,恐時日不多,鳳仙便放小蓮回去照顧,臨了,盡盡做女兒的孝心。
“姐姐冰雪聰明,必然一學就會。”杜梅笑着看她。
“算了,我怕是學不來的,我們還是前頭喝茶去吧。”鳳仙咬了下嘴唇說。
一連三天過去了,杜梅每日到宋府中,把脈艾灸,調理飲食,鳳仙的病越來越有起色。可柳更生和麥冬卻一點消息都沒有。
杜梅心知此事急不來,隻得耐着十二分的性子,她閑下來就繡豬寶。三天,一隻憨态可掬的豬寶,就擺在了那對福豬中間。鳳仙對這一家三口非常滿意,經常拿出來把玩。
這日清晨,柳更生來得比往日都早,待杜梅上了馬車,他悄聲說:“今兒,趁打點的人當班,我帶你去見見他們吧。”
“好啊,好啊。”杜梅一疊聲地說,她正日夜盼着呢。
進了清河縣,也不到鳳仙家去。柳更生将馬車藏在一個僻靜的巷子裡,因消息來得突然,杜梅也沒準備什麼吃食,隻得在沿街店鋪裡買了現成的包子牛肉。
柳更生帶着杜梅有意避着人,專撿曲裡拐彎的小路,穿街過巷,終于來到了清河縣縣衙大牢。
因着一大早,街市上人迹
寥寥,門口把門的衙役似乎早得了消息,收下杜梅塞過來的一串銅錢,眼皮眨都不眨地,把頭偏到了一邊。柳更生趁勢帶着杜梅一閃身,進了大門。
“韓頭,給你添麻煩了。”越往裡走,越昏暗,油燈的煙氣太大,不僅看不清,還熏得人喘不上氣來。柳更生朝着一張桌子後面的人,點頭哈腰地說。
“嗯,動作麻溜的。”桌子後面站起個八尺高,虬髯黑面之人,聲音啞如悶雷。
“快點。”柳更生小聲催促杜梅。
這一路上,從進門到這裡,不過幾十丈遠,卻有門禁七八道,杜梅不停地掏錢,都掏麻木了。
“哦,孝敬您的。”杜梅遞上兩張面值一百兩的銀票,她已經将五百兩銀票兌換成一百兩一張的了。
“跟我來。”韓牢頭接過銀票,看都不看一眼,直接揣在懷裡,他轉身在牆上摸索出一串鑰匙,一路甩着嘩嘩響,走在幽暗的大牢裡。
“我是冤枉的,冤枉的!”
“救我,快救我!”
……
關在監牢裡的人,在死寂中聽到鑰匙的聲音,立刻如同瀕臨死亡的人得到長生不死藥一般,全部湧到甬道邊,大聲呼号。
“不想吃午飯的,盡管叫!”韓牢頭輕聲說了一句。他的聲音暗啞清冷,如同來自地獄。
那些囚犯一聽他的聲音,仿佛潮水般,瞬時退回監牢的角落裡。隐在暗色中,極力減少存在感。
“就是這裡了,你們隻有一炷香的工夫。”韓牢頭揀出一把鑰匙,咔嚓一聲,鎖就打開了。
柳更生給杜梅遞了個眼色,他陪着韓牢頭到一旁抽煙唠嗑去了。
“牛哥!黑哥!”杜梅踏進牢房,将吃食擱在桌上,隻見兩個人背身睡在草堆上。
“杜梅?真是你!”牛二聽到熟悉的聲音,一骨碌爬了起來。
“起來,黑泥鳅,我說什麼來着,杜梅一定會想辦法救我們的!”牛二踢了下旁邊睡着不起的黑蛟龍。
“黑哥這是怎麼了?”杜梅覺察出異樣,按理說,黑蛟龍有老婆孩子,該比牛二更着急才是。
杜梅探身捏住了黑蛟龍的手腕:“他發燒了!受傷了?”
“嗳,說來話長,這監牢裡原住着其他人,他們欺負我們兩個,前兒半夜裡搞偷襲,黑泥鳅被打破了頭,今兒竟然發燒了,這可怎麼辦?”牛二焦急地抱住黑泥鳅,輕輕呼喚。
“死不了!我就是睡得死一點。”黑泥鳅有氣沒力地說。
“你這怕是要化膿了。”杜梅掀開打結的頭發,看了看傷口。
“能不能活着出去都不知道,還怕什麼化膿?”黑蛟龍自嘲地說。
“你瞎說什麼,龐嫂子和小寶還等着你呢。”杜梅聽了他的話,一下子覺得如鲠在喉。
“隻苦了他們了!”黑泥鳅歎了口氣,困意襲來,他又閉上了眼睛。
“我一會兒多給韓牢頭一些錢,讓他好歹給黑哥弄點藥吃。”杜梅又細細把了次脈,低聲說。
“外面什麼情形了?”牛二知道杜梅進來一趟不容
易,不知花掉了多少錢。
“聽說很多衙門裡的人都上了寒凍山,那山裡到底藏着什麼呢?”杜梅疑惑地問。
“寒凍山?不可能,不可能!那山其實不大,遠不如射烏山。我們小時候常去玩,山上哪旮旯長蘑菇,那旮旯出筍子,我們門清。”牛二瞪着牛眼,不相信地說。
“不說那些了,你們在這裡如何?”杜梅看牛二并無傷痕,想來審訊并未用大刑。
“縣老爺也就提過一次審,卻日日留我們在這裡吃牢飯!”牛二坐在桌邊,也不客氣,拈起包子牛肉,自顧吃起來。
“看來這事怕不好弄,縣老爺也做不得主。”杜梅蹙眉。
“妹子,謝謝你能來看我,我在這裡待着無事,想過各種結局。活,我之幸,死,我之命也。”牛二擰眉說道,仿佛參透人生。
“牛哥,千萬不要這樣說,但凡有點希望,我都是要幫你們争取的。”杜梅聽了他的話,心中一片黯淡。
“還是把那活命的錢留給活人吧,你告訴我家裡,我把錢藏在我床底下的磚頭下面了。”牛二知道杜梅現在花的,肯定都是她自己攢的錢。
“牛哥,你也别洩氣,天無絕人之路,你把黑哥照顧好,外面我盡力為你打點,總有出去的一天。”前途渺茫,杜梅不知道說什麼是好,隻得盡量安慰道。
“妹子,我孑然一人慣了,生死早已看淡,唯我老娘可好?”牛二惦記家人。
“嬸子、嫂子還有牛三都好,他們隻盼你也好好的。”杜梅想了想,把媒婆的事,撇在一邊不說了。
“黑泥鳅家裡呢?”牛二看了眼昏睡在草地上的黑蛟龍。
“龐嫂子和小寶也好。”杜梅絕口不提田地難賣的事。
“那就好,那就好。”牛二突然淚流滿面。杜梅報喜不報憂,他哪裡不明白。
“咳咳咳,時間到了。”韓牢頭的聲音冷得讓人打寒顫。
“去吧,去吧。”牛二雖是不舍,但還是含笑朝杜梅揮揮手。
“我過些日子再來看你。”杜梅小聲地說,慢慢走出監牢。
“韓牢頭,麻煩你給黑蛟龍弄點藥吃吃敷敷,他傷口化膿,發熱了。”杜梅又遞出一張銀票。
“這人對你很重要?”韓牢頭收下銀票,悶聲問。
“不,他對他的老婆兒子很重要。再說,若他真死在監牢了,想來您也不好對縣老爺交代吧。”杜梅擡眸看看韓牢頭。
“你這丫頭好一張利嘴!放心,我自是不會讓他死的!”韓牢頭睨了眼杜梅。
“你怎麼敢這樣跟他說話!”走在暗沉的甬道裡,柳更生低低地埋怨。
“他隻是牢頭,又不是閻王!”杜梅走出大牢,終于呼吸到新鮮空氣,她不禁大口呼出一口濁氣。
“你可知道他的诨名就叫韓閻王!任誰進了清河縣大牢,沒有不乖乖吐口的。”柳更生一副劫後餘生的模樣。
“作奸犯科者自然懼他,我有何怕的?”就要拐彎,杜梅回望大牢大門,宛如一個巨獸張着的血盆大口。2k閱讀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