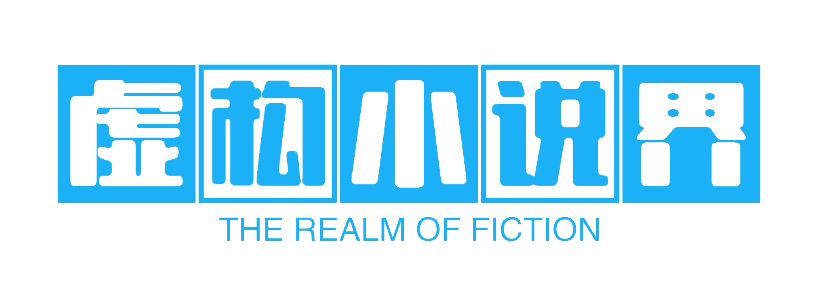江濤看着她,“可畫,你知道他們是什麼人嗎?一旦招惹上他們,後面的事情就不是你能控制的了。”
“哥,我已經等了十二年,我爸爸已經五十多歲了,如果我再不去找他,不問出當年的真相,我不知道此生還能不能與他見面,會不會留有遺憾。但我現在連他被關在哪兒都不知道。”
“你爸入獄的時候你年紀小,但媽肯定是知道真相的,難道她一點都不願意告訴你關于你爸爸的真實情況?”江濤問道。
可畫搖搖頭,“想必媽媽是恨極了他,從不肯提起,更不會允許我去找他。況且她現在過得很好,能從抑郁中走出來不容易。我也不想再喚起她那些痛苦的記憶,就讓我一個人折騰吧。”
“相關部門也查不到嗎?”江濤問道。
“我和媽媽的戶口本早就和爸爸分開了,我去查需要有直系親屬的關系證明,勢必會牽扯到媽媽,那将會是一個非常嚴重的惡性循環。”
江濤深深地呼出一口氣,去酒櫃拿了一瓶紅酒,放在托盤上,遞給可畫。
他們一起上了電梯。
“五零九包廂,裡面有四個男人,坐在正位的就是我們說的人。你一定要小心,有事就喊我。”
可畫看看那瓶紅酒,“哥,這酒多少錢?”
“三萬多吧。他們平時比較喜歡點這款。”江濤說。
可畫撇撇嘴,心想夠她一年的房租了,“告訴你們老闆,這酒錢我後面還他。”
江濤看着可畫,“我會給的,放心。”
到了五零九門外,可畫把自己的大衣遞給了江濤,一隻手拿着托盤,另一隻手去敲門。
她聽到裡面有人回答,才推門進去。
這是她第一次來這種地方,包廂裡的光線很昏暗,她稍微适應了一下,便環顧四周。怎麼看都不隻是四個男人,确切的說,是四個男人和三個女人。
可畫心中已了然,有喝酒的就有陪酒的。
離門最近的男人穿着件白襯衫,最先看到她,“呦,這個不錯,戰哥,你看看。”
可畫順着白襯衫男人的目光望過去,他叫戰哥的那個男人坐在正位上,隻有他的身邊是空的。
還缺一個女人。
他輕輕轉了下頭,掃視了可畫一眼,說了句,“看不清。”便低頭看手機。
包廂裡放着音樂,還有人在對着屏幕唱歌,但這句話,可畫還是聽清了,那聲音似乎很有穿透力。
穿白襯衫的男人叫向天,他笑着對可畫說:“你還杵在那兒幹嘛?還不快過來,讓戰哥看清楚。”
可畫走到陸之戰對面,把酒輕輕的放到桌子上。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她身上,她覺得自己有點像馬戲團裡的小醜。
她有一刹那的局促,一個呼吸的功夫便又恢複了平靜。她早就學會了波瀾不驚,所有的緊張和恐懼,都在十四歲那年用完了,從那以後,她便成了現在的性子。
她在陸之戰對面的桌邊蹲下來,拿起開瓶器,安靜的去開那瓶紅酒。
“擡起頭。”
可畫聞聲看過去,目光落在陸之戰的臉上,她們對視的刹那,可畫看清了坐在對面的男人。他很英俊,高挺的鼻梁,棱角分明的五官,以及眉眼間不可一世的霸道。
她輕輕彎了彎唇角,這人看着和她的那些刺頭學生有點像。然後又專心的去開那瓶紅酒。
陸之戰沒說話,他還挺喜歡她眼裡的光,和微笑的唇。
大家都明白,以他的性格,沒有趕人那就是滿意了。
向天說,“你去坐到戰哥身邊,酒我來開。”
可畫沒回答,也沒停下手上的動作,她很快就取下了瓶塞,笑着拿在手裡,對着向天晃了晃,意思是已經好了。
她拿起白色的餐巾包在酒瓶外面,走到陸之戰面前,傾身給他倒了一杯,然後輕輕的放下酒瓶,安靜的坐到了他旁邊。
另外那三個男人彼此交換了下眼神,看來這姑娘有些小聰明,故意隻給陸之戰一個人倒酒,擺明了她今天的眼裡隻有他。
陸之戰拿起酒杯喝了一口,唇角微彎。那位白襯衫笑了笑,“戰哥,這姑娘什麼意思?連我們的酒都不給倒。”
陸之戰側頭看了她一眼,正好可畫也在擡頭看他,四目相對,眼裡的星光流轉,平添了些許暧昧出來。
陸之戰沒說話,自己拿起酒瓶給向天倒了一杯酒,“這樣可以嗎?”
另外兩個男人也開始起哄,“戰哥,你不對了,這麼快就開始護着了,還真是活久見。”
向天也開始起哄,“今晚可有好戲看喽。”
可畫不說話,一直安靜的坐着,陸之戰把手搭在她的肩膀上,湊到她耳邊輕聲說,“你想要什麼?”
可畫的心裡顫了顫,以前還從沒和男人這麼親密過,她看着他的眼睛,思考着他問的這句話,是什麼意思。
是問接下來的好戲,她需要什麼才肯,還是問她進來這裡的目的。
她看着陸之戰,微笑着問:“你指什麼?”
陸之戰笑了,他笑起來很好看。
他把酒杯放到桌子上,“你覺得我指的是什麼?”他點了一根煙,“不管指什麼,你都已經坐在這裡了。”
可畫明白了他的意思,他在問她想要什麼,又願意付出什麼。
她輕聲說,“我有一個請求。”
陸之戰看了她一眼,“哦?不妨說說,我也掂量掂量,免得出不起。”
可畫盯着他的臉,不想錯過他臉上的任何表情。“我想得到一個人的消息。”
陸之戰沒說話。
其他人都好似沒聽見,各自忙各自的。可畫知道自己此時有些不識擡舉,即使他問,她也不該實話實說。
可她今天的目的就是求他幫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