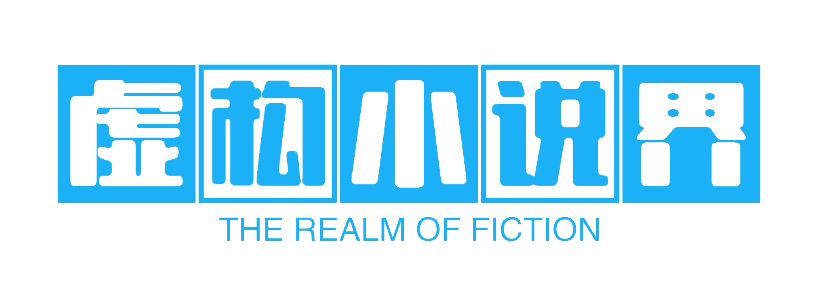第三十章
第三十章
糊糊洗掉, 蘇毓趁機在徐宴臉頰上摸了一把。特麼的,比她的滑。
徐宴被她蹭的一頓, 低頭看着她。
蘇毓臉色郁郁地撇過頭:“無事, 突然發現我做得面膜效果确實非常不錯。”
徐宴右手食指刮了一下被蘇毓摸過的臉頰,眼中閃過細碎的笑意:“嗯,效果确實不錯。”
蘇毓:“……”
徐宴偏過臉, 整了整衣冠, 将鬓角濕潤的發梢捋到耳後。
敷面膜敷了一刻鐘,這會兒洗掉再收拾妥當又是半天過去。徐宴擡眼看一下窗外的天色。有些泛黑, 陰雨綿綿了一整天, 院子裡到處是泥濘的泥水。
離開學還有兩個月左右, 屆時入學還有一次考核。
豫南書院與别的書院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們将學子按資質分出三六九等, 分别由不同的老師教導。徐宴被分在甲班是不錯, 但這也不是定死了往後就在甲班。若是徐宴後期的考核不達标, 一樣會被剔出甲班,落到後頭的班級裡去的。
徐宴是不在意這些的,他自幼學習讀書都有自己的一套方法。先不說别人适不适合, 但對于他自己, 是十分有效率的。
換言之, 光是讀書和做文章他自己足夠自律, 并不依賴别人的教導。而徐宴之所以會選擇進豫南書院, 并非貪圖豫南書院的名聲,而是因為他渴求更大的書庫和閱讀量。
寒門學子就算再聰慧, 沒有家族的底蘊支撐一樣是成不了事兒的。徐宴心裡很清楚這一點, 所以在盡自己最大的可能去夠到藏書量大的書院門檻兒, 為自己創造條件去博覽群書。
“再過三日是南城清風堂的字畫局,你可要去?”蘇毓想去字畫局試一試, 徐宴答應了便會放在心上。
蘇毓正在洗頭發。她這個藥膏的效果是有目共睹的,如今徐宴也不覺得她往腦袋上糊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可笑了。甚至蘇毓偶爾忙起來忘記的時候,他還會提醒一下。
“嗯,”蘇毓慢吞吞地往頭發上澆水,想想,又問,“宴哥兒,你是不是進去過?”
徐宴點點頭:“去過兩回,不多。”
這倒是蘇毓沒想到的,她還以為徐宴這厮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隻讀聖賢書呢。将濕頭發盤起來用布巾子包起來,蘇毓擡起頭:“裡面是怎麼叫賣字畫的?可有什麼規矩需要注意?”
蘇毓知道字畫局還是一次意外她去書局買筆墨,不經意間聽到兩個書生談及此事。上前仔細地問過,才曉得金陵字畫局的傳統。但很遺憾,身為女子,她連大門都進不去。
“沒别的苛刻要求,隻一點,”徐宴是被人請着進去的,雖不太感興趣,但進去以後也多少了解了些字畫局的規矩,“字畫必須公開展示,需得到字畫局三位以上評委的一緻認可方可售賣。且字畫的起價不是由自己定,而是評委根據自我的判斷商量來定。”
蘇毓聽完,覺得這标準有些太随性:“有沒有評委被賄賂,惡意定少的情況發生?”
這徐宴就不清楚了:“評委都是金陵的書畫大家,行事定然得愛惜羽毛。”
……說的也是。
蘇毓放心了。其實也不能說放心了。而是,她的書畫水平就在那,能買出高價是她的幸運,賣不出去,那也隻能說技不如人。本身就是去碰運氣,蘇毓也就沒考慮那麼多。
當日夜裡,蘇毓就跟着徐宴去了書房。
因着蘇毓要作畫,徐宴便将自己的書桌讓出來給蘇毓用。
他挑了兩本書,娴靜地在蘇毓的旁邊盤腿坐下來。不知為何,徐宴在專注地做自己的事情。蘇毓卻總有一種随着時間流逝,身旁徐宴的存在感越來越強的感覺。明明這厮很安靜來着,但就是氣息、聲音和影子都籠罩着她,讓蘇毓隐約之中有種被什麼東西給盯住了的錯覺。
徐宴安靜地翻着書,蘇毓便慢吞吞地研墨。
曾經幼年,蘇毓的祖父是極擅長畫山水的。蘇毓跟着祖父長到十二歲才被父母接到身邊,自三歲開蒙起就拿毛筆學丹青的蘇毓,下筆自然也是擅長山水。不過後來被母親逼着學了一段時間的水粉和油畫,蘇毓的山水又多了一點奇幻色彩。
真真論起來,蘇毓的畫大概是水墨為主,但又混合了水粉和油彩的特點。比起原本華族水墨喜歡留白的特性,她的畫拿出來就很會顯得瑰麗。
徐宴的書房沒有顔料,朱砂倒是有些。蘇毓隻能就着朱砂和墨簡單地畫上一幅。
見識過廣袤的草原和極地的冰川,見識過一望無際的星空和飛流直下的瀑布,更見識過終年不化的雪山和漫山遍野的山花……蘇毓滿腦子花開的盛景。她下筆畫的也比較随意,勾勒得是一幅明月之下,瀑布濺起水霧的草叢開滿山花的場景。
畫的随意,用了些水粉畫的下筆方式。但隻是須臾,這瑰麗的場面被勾勒出來,蘇毓聽到耳邊徐宴的呼吸聲輕了。她沒回頭,沾了點朱砂,用水稀釋,天上雲彩和草叢的顔色疊加,少許地點綴。
等一幅畫畫完,差不多一個鐘頭過去。蘇毓擡起頭,感覺脖子咔咔地響。
徐宴不知何時意境放下了書,就坐在旁邊盯着桌面上的畫作。
這種水墨混合水粉的畫法,近景遠景的自然過渡,光與色的明暗對比,是這個年代所沒有見過的。但不得不說,這種畫法比金陵城細線勾勒邊緣的畫法要夢幻太多。那種自然的意境感,哪怕不曾親眼見過畫中之景,也有一種撲面而來的身臨其境的錯覺。
“……這是你跟誰學的畫法?”徐宴雖也會畫,但不曾系統學過,識貨的眼力還是有的。
蘇毓轉手腕的動作一滞,小心翼翼地回:“我自己琢磨出來的。怎麼了?”
徐宴頭伸過來,貼得更近了。
蘇毓隻覺得自己鼻尖全是這厮身上清冽的氣息,心不自覺緊繃起來。徐宴卻好似不知,雙目緊緊盯着畫面上開闊又絢爛的景色。似乎很難相信,這是一個不曾拿過筆的婦人下筆畫成的。
“沒,”徐宴将畫小心地拿起來,仔細地端詳,“畫的很不錯,不像是十多年不曾拿筆的。”
蘇毓心裡一咯噔,慢慢抿起了嘴角。
徐宴隻說了這一句便沒多說什麼,安安靜靜地觀賞着畫中的花海。徐宴向來覺得,胸有丘壑之人眼中所見之景皆是美景,胸中所含之意全是美意。他從前從未探究過毓丫的内心世界,這還是頭一回發現,毓丫的心中藏着如此美麗的景色。
他心中鼓噪着什麼,驚覺自己如此的淺薄和自負。因為自負低估身邊人,所以哪怕毓丫在他身邊十多年,他也不曾發現她心中藏有花海。徐宴突然很有些羞愧。
蘇毓看他專注地欣賞着畫作,心裡有點虛。畫确實是她原創,但水粉畫可不是她琢磨出來的。
看了許久,他将畫慢慢卷起來,自然而然地放進了自己的箱籠。
蘇毓:“……”
見他臉色不大好看的樣子,雖不清楚他心裡想什麼,但她很有眼色地沒開口去刺激他。
自這之後,蘇毓總覺得徐宴給她的存在感更強了。這日夜裡睡下時,徐宴的目光也會若有似無地落到她的身上。
偶爾蘇毓看過去,徐宴又沒有在看她。
蘇毓:“……”罷了,愛咋咋地吧,有本事就将她拖出去燒了。
燒是不會燒的,徐宴還在反省自己。
并且反省得很深刻。
次日,徐宴有事要出門。出門時走得急,差點撞上一個姑娘家。若非他躲閃得快,定然會撞上。不過那姑娘還是吓了一跳,胳膊肘挂着的籃子掉地上,紅薯滾了一地。
徐宴忙蹲下去幫她撿起來,全裝好了擡眼,見是張家的那個二姑娘。
張家二姑娘低垂着眼簾不敢看人,說話聲音也細細的:“無礙的,是我走路沒看清楚,不賴公子。”
徐宴點點頭,沒多言,拿着書便匆匆離開了。
人走遠,那低着頭的張二姑娘才微微擡起眼簾。
她盯着徐宴遠去的背影,揉着通紅的臉頰。似乎看得久了,臉上竟然還有些癡意。正好這時候徐乘風抱着一個小藤球在院子裡跑,看到了,小眉頭皺起來。
他雖然年紀小,但早年跟徐宴在鎮上見到這樣的女子多,也知道這些眼神的意義,這都是對他爹圖謀不軌。
于是他屁股一扭,就跑去屋裡找蘇毓。
他哒哒沖進屋的時候,蘇毓正在整理衣裳。看他滿臉的不高興,随口問了一句:“怎麼又嘟着嘴?”
小屁娃子哼哧哼哧地拖了一個小馬紮過來,在蘇毓的腳邊坐下:“娘,你說為什麼那些人都用那種黏糊糊的眼神看着爹呢?”
蘇毓手一頓,詫異地低頭看過去:“誰拿黏糊糊的眼神看你爹了?”
“就張伯娘家的姐姐啊,”徐乘風如今是蘇毓的衷心小尾巴,耳報神當的那叫一個順溜,“她每天都在院子裡站着,爹出門,十天有八天都能碰上她。”
這事兒蘇毓還真頭一回聽說。
事實上,徐乘風不說,蘇毓沒往這方面想,但他這麼一說,蘇毓免不了就想起來。她這段時日也碰到過幾次張家那二姑娘,每回那姑娘都穿得花枝招展的,一聲不吭地站在院子裡。她原先還當她在幹什麼呢。原來是在看徐宴嗎?王家莊頭牌這麼快就招來了蝴蝶?
蘇毓摩挲了一下下巴,覺得好笑又無語。徐宴妻子兒子都有了,怎麼這些姑娘還總不消停呢?
關于這事兒,徐宴自己也想不通。
比如他立在書局的大堂,面無表情地看着眼前的紅衣裳小姑娘。
紅衣裳小姑娘也不是旁人,正是那回在金陵城外的破廟裡遇到的那個暴脾氣的勳貴千金。此時她的身邊跟着四個體面的仆從,一左一右的護着她不叫人碰到。右手邊還站着一位相貌堂堂的年輕公子,錦衣華服。
她擋在徐宴的面前,一臉驚喜的表情看着他:“是你啊!”
甄婉是真的喜出望外,她惦記這人許久了,沒想到會在金陵城碰到。甄婉還是第一次這麼惦記一個人,若非此時人在外面,她就要伸手去抓徐宴的胳膊了:“你怎麼會在這?你是來求學的嗎?哪家書院?”
徐宴是來還書的,前幾日在這裡借的書看完了,此時是來還書的也是重新借書的。
一看見她就想到了那夜刺骨的潭水,還有他高燒幾日不退隻能喝粥的場景。徐宴這素來不鹹不淡的人看她眼神格外的冷冽,完全沒有與甄婉相遇的驚喜:“嗯,甄姑娘。”
他不回答,甄婉也不會在意。她雖說嬌蠻任性,但對徐宴的容忍度還是很高的。甄婉私心裡就是喜歡徐宴這股高傲勁兒。
書局裡的人漸漸多了,有人想要去二樓拿書,路被人擋着,此時隻好立在兩人旁邊等着。
徐宴見狀,忙拿起書往旁邊走開。他才一走動,甄婉腳下就不自覺地跟着他走動。她旁邊那位華服公子也不出聲制止,隻是亦步亦趨地跟着甄婉。
甄婉身邊一群人讓開了,立在旁邊等着的書生們雖然好奇,但還是收了心思上樓去。
走至旁邊,甄婉還興高采烈地在徐宴耳邊嘀咕:“婉兒那日走得匆忙,還未請教公子尊姓大名。那日夜裡是婉兒任性胡鬧了,深夜亂跑摔進湖水裡。害得公子為了救我寒冬裡下水,也不知公子那日起身後身體可有礙?若是有礙,可有好好瞧過大夫?說來,都是婉兒的罪過。婉兒如今就在金陵,救命之恩無以為報,往後若是公子有難處,大可以來金陵柳家來尋我……”
“對了,還未請教公子尊姓大名?”甄婉像一隻翩翩起舞的蝴蝶,整個人洋溢着興奮的情緒。
徐宴聽她喋喋不休,心裡其實有些煩躁。不過他這人素來喜怒不形于色,哪怕覺得厭煩,面上也是丁點兒看不出來的:“甄姑娘,若是無事,徐某還有事要做。這就告辭了。”
“徐?”甄婉像是沒聽到徐宴後面的話,她見徐宴要走,到底還是伸出手去抓他袖子了,“原來你姓徐?徐公子叫什麼名呢?可否告知婉兒?”
徐宴眉心微微蹙起來,臉色更淡了。
尚未張口,甄婉身邊的華服公子倒是先開了口。語氣聽着輕飄飄,卻藏不住一股子居高臨下的傲慢:“徐公子幸會,在下是金陵郡守柳家的嫡次子柳之逸。這位是在下的表妹,京城将軍府的姑娘。”
徐宴聽到這,翻書的手一頓,擡起頭來。
方才他都不曾仔細看過,此時才仔細打量這個華服公子。一張刀削斧鑿的俊臉,高鼻梁,大眼睛,削薄的嘴唇緊抿着。與徐宴清隽俊逸相比,他生得一幅偏男子俊朗堅毅的皮相。不是說不夠俊俏,隻是身邊有徐宴這麼個太灼目的人襯着,顯得不那麼起眼了起來。
徐宴是猜到了眼前這姑娘身份不簡單,但沒想到會是三品高官的子嗣。他微微掀起眼簾看向了甄婉,這才注意這姑娘是個美人坯子。柳葉眼,媚如絲,瓊鼻秀目,雖還未完全長開,但可見往後美貌。
收回目光,徐宴找了個位置坐下。擡手示意了對面的椅子,請兩位坐下。
華服公子看了一眼甄婉,撩袍子在徐宴對面坐下。甄婉其實更想挨着徐宴,但被柳之逸掃了一眼後,嘟着嘴坐到柳之逸身邊。
甄婉落水的事情,在她連夜被送到金陵城時柳家人就都知曉了。
關于這次徐宴對甄婉的救命之恩,柳家人雖沒有親眼所見,但聽甄婉手舞足蹈地描述,柳家人尤其是柳之逸連徐宴當時救她的表情和動作都一清二楚。柳之逸以挑剔的目光上下打量着徐宴,不得不承認一件事,這人生得是真的貌美。
“徐公子是來金陵求學的?”柳之逸手指點了點桌子,笃笃地兩聲。
徐宴點頭:“嗯。”
“哪家書院?金陵有不少書院,但門檻兒都挺高。寒門弟子想入好的學院,怕是有點難。”柳之逸說話強調淡淡的,不像徐宴是情緒的淡漠,他是有着一種輕慢的冷淡,“不過如今還沒到開課的時候,徐公子若是沒找到入學的學院,柳家不是不能出手。”
“不必,”徐宴阖上書頁,“我已經入學了,等着開課罷了。”
“哦?哪家?”柳之逸又問了一遍,他對徐宴就讀的學院很是在意。不知為何,他直覺地很讨厭眼前這個男人。相貌出衆,氣度卓然。明明就是出身草芥,區區一個鄉下窮書生罷了,憑什麼?居然在他一個高官子弟跟前坦然自若,毫不膽怯,哪兒來的底氣!
“豫南書院。”
柳之逸臉上的倨傲頓時僵硬了。
他坐姿沒動,卻收回了搭在桌案上的手,緩緩靠在了椅子靠背上。那雙倨傲的眼睛直勾勾地帶着審視意味盯着徐宴,似乎在懷疑他話裡所說事情的真實性。
事實上,柳之逸哪怕作為金陵太守的嫡次子,也沒能通過豫南書院的考核。比起其他道聽途說的人,真正參與過考核的人才知曉豫南書院有多難進。尤其徐宴還是寒門子弟,單槍匹馬一人來。能被豫南書院錄取,就等于表明了一件事,這是個未來的能臣。
徐宴垂下眼簾,複又擡起來。一雙清淩淩的眼睛,沒有絲毫的心虛。他說出口的話,神情淡漠得仿佛剛才說出自己是豫南書院學子的話跟今日吃了什麼一樣輕易随便。
甄婉眼睛噌地一下就亮了,亮晶晶的:“豫南書院?你居然是豫南書院的學子?!”
哪怕遠在京城,甄婉也聽說過豫南書院的鼎鼎大名。豫南書院自建立以來,至少有四百年的曆史。裡頭的教書先生,哪一個拿出來不是當世大儒。這書院出了太多進士,名聲小的且不說,就收京城有多少官員是豫南書院的學生,前朝和今朝的能臣皆出自此學院。
說句大逆不道的話,天子門生的名聲都不一定及豫南書院學子有牌面,尤其入了這個學院的寒門子弟。
“徐公子,”甄婉突然覺得眼前之人更灼目了,仿佛渾身在放光,“你,你……”
她有些激動,一種撿到寶的激動。本以為隻是個皮相好性子對胃口的俊俏書生,沒想到是個滿腹經綸的。甄家是武将之家,甄婉自幼見多了舞刀弄槍的漢子,就偏愛那些文雅清隽又才貌雙全的男子。這一出門就碰上了一個厲害的,怎麼能叫她不激動萬分?
此時她已經顧不上徐宴有妻有子,想着若他真是豫南書院的學子,即便身份低了點,将來也會一飛沖天。甄家不是那等狗眼看人低的人家,徐公子隻要拿出本事來,也不是沒機會當甄家女婿。
“……徐公子,你如今可缺什麼?那日你救我,本該當日就感謝你。”甄婉絞盡腦汁的,想要表達一下自己的心意,想要向徐宴示好,“隻是那日之後我傷寒多日未愈,沒能有所表示。如今提及是有些晚了,還請徐公子見諒,不要因此誤會于我。”
“無礙,不是什麼大事,舉手之勞罷了。”徐宴已經不耐煩了,他對眼前兩個官宦之家的子女并不感興趣。甄婉也好,柳之逸也罷,統統與他無關。
“若無其他事,二位不如……請?”很直白地趕人。
柳之逸打量了他許久,有些不信,但又不敢輕易開口得罪。
若當真是多才之人,柳家自然樂得交好。柳家在金陵是尊貴,其實并非家族底蘊身後的官宦世家。在舅父甄正雄官居三品之前,柳家的家主也不過一個七品小官。後來借着甄家的勢,才爬到了金陵郡守的位置。家族的地位不夠穩固,他們在外也不太敢肆意妄為。若眼前之人當真是個可造之材,機緣巧合地與柳家有了關聯。他們自然是拉攏的。就算拉攏不成,能不交惡自然不交惡。
“既然如此,那徐公子你且溫書吧,我們還有事。”柳之逸心氣兒有些不順,但還是不想為了莫須有的不順眼惹事兒。他一把扯起賴着不想走的甄婉,起身便準備告辭。
柳之逸此行來這書局,本是為了買幾本書回去。方才一進門,甄婉就領着人往徐宴跟前沖,還沒來得及挑。這會兒起身告辭,轉頭去挑書了。
甄婉不想走,但柳之逸手下用了點巧勁兒,将人給拽走了。
人一走開,徐宴就阖上了書。
去掌櫃的那兒做了登記,多接了幾本書也轉身離開。被拉到一旁的甄婉盯着徐宴的背影看了許久,幽幽地吐出一口氣:唉,要是徐公子沒娶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