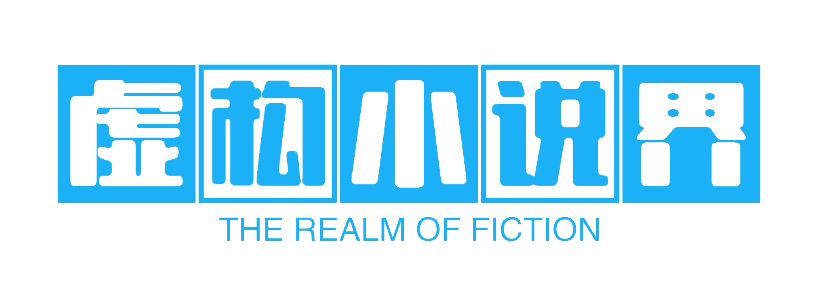第一百二十七章
第一百二十七章
正宮突然冒出來一個皇子, 這消息不亞于憑地一道驚雷劈在了某些人頭上,尤其是晉淩钺。晉淩钺前段日子才被武德帝當衆叱責心胸狹窄, 不堪大任。這才沒多久, 就有一個五六歲的毛孩子挂到的中宮名下,硬生生折騰出個中宮嫡子來!
若當真是白皇後所生,那另當别論。晉淩钺不至于如此意難平, 但這孩子根本不是。這就是個冷宮瘋子所生的孩子, 生母出身卑微,連個嫔都不是。人瘋了七八年, 孩子走大運被人發現給領到人前來了。這不知道打哪兒來的孩子一冒出來就給定到皇後名下, 就這麼成了中宮嫡子。
“哈?”晉淩钺屋裡東西砸了一片, 地面上全是碎片, “本殿自來不信運道這種東西!不知打哪兒冒出來的小野狗, 毛都沒長齊呢, 也配與本殿搶東西!”
“殿下息怒,殿下息怒……”仆從跪了一地,趴着祈求他平息怒火。
耳邊嘩啦嘩啦的瓷器碎裂的聲音, 誰都不敢上去攔。
客卿們人擠在外間, 七嘴八舌地勸解。可晉淩钺正在氣頭上, 話都聽不進耳中, 人根本冷靜不下來。正當衆人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 其中一個藍衣賞的年輕男子搖着扇子走上前,忽然笑道:“不過是多了個孩子, 才六歲, 長不長得大還另說, 哪裡值當殿下如此動怒?”
晉淩钺身子一頓,轉過身, 蹙眉看向他。
那藍衣賞的年輕男子正是廖原,是國公府的客卿。不過這段時日,晉淩钺被諸多事情纏上來,焦頭爛額。廖原便被蘇威委派到禹王府,替禹王做事。
隻見他搖着折扇,擡腿便跨進内屋:“殿下,您這是着相了。”
廖原此人年紀不大,但城府極深。長着一張人畜無害的俊臉,說話溫溫和和的極會哄人。若是一般人與他說話時候得萬分留心,稍不留神便會被他套取話去。換言之,這就是個奸詐的狐狸。
做事心狠手辣,不留餘地,還十分不怕死。一個連禹王都感歎藝高人膽大的貨色:“嫡子又如何?記在皇後名下又如何?等他能真的聽懂人話,至少也得十年後。”
他走得優哉遊哉,說話有股蠱惑人心的味道:“皇後多年身處後宮,名聲再好,也不過是個手無縛雞之力的婦道人家。她一沒位高權重的娘家幫扶,二沒有權臣支持。哪怕陛下當真立中宮這小皇子為儲,這也就是個活靶子罷了。再來,若是陛下當真避長立嫡,那不過是表明了一件事。”
晉淩钺心裡一動,眉頭擰出了一個結:“父皇根本不願立儲。”
“是的。”
說到底,這還是晉淩钺與武德帝父子之間的争端。武德帝如此忌諱已經長成的兒子,甯願從冷宮裡拎出一個無權無勢無依無靠的孩子記到皇後名下去立儲也不願立他為太子,就是不想讓權罷了。
廖原挑明的東西,晉淩钺如何不明白。
“殿下與其為了一個六歲孩子大發雷霆,不如想法子打消陛下對您的戒備。”廖原是當真藝高人膽大,旁人不敢說的話,他眼眨不眨地就說了,“畢竟殿下下手除掉一個中宮嫡出,還會有更多的中宮嫡出。隻要陛下一日不消除對您的警惕,這種事就永遠不會少。況且……”
他勾唇一笑:“如今這個孩子對殿下來說,算是最好應付的一個傀儡。這個孩子無依無靠,除中宮那位能庇護一二,一個能頂事兒的靠山都沒有……”
若是換了旁人,那就不一定有這個恰當。
後面的話他沒說,但晉淩钺聽懂了弦外之音。
确實,沒有比目前這個‘中宮嫡子’更好應付的了。再來一個中宮嫡子,基本都是母妃健在的。且各宮宮妃的娘家可不像這個“嫡子”這般好對付。一旦有一個被立為儲君,别說後宮裡蘇貴妃的地位受到威脅,朝堂上那些慣會見風使舵的朝臣們,心思怕是也會跟着搖擺浮動。
這人心一浮動,總有人會亂站隊。屆時朝中勢力也跟着重新分割,他還能否穩住如今這般局勢,那就當真懸了,得不償失。
這般一琢磨,禹王的眉頭就舒展開來。他将手裡的花瓶放下,轉過身,細細地思索了起來。
與此同時,天香樓裡,徐宴拿到了一份名冊。
六月中,窗外樹上的知了吱哇吱哇地吵得人心浮躁。徐宴端坐在桌案後面,垂眸凝視着這名冊上的人名兒。其中大多數已經被晉淩雲當場賜死。
他目光落到倒數第三倒數第十個上,一個叫雲秀,一個叫芳兒。兩個人都是晉淩雲身邊得力的人。一個還在晉淩雲身邊伺候,一個見了血被吓唬得神志不清,人被送出公主府。如今人已經不在京城,瘋瘋癫癫地被娘老子帶着一道去荊州投奔親眷了。
“除了這些人,還有沒有漏網之魚?”徐宴的嗓音仿佛這桌案上的青煙,缥缈又無情。
桌案的正對面坐着一個圓臉的中年婦人。
這婦人不是旁人,正是長公主府的掌事嬷嬷吳嬷嬷。十多年前皇後撥給晉淩雲跟着她出嫁,之後便一直在晉淩雲身邊伺候。不過跟了晉淩雲多年,就隻認白皇後一個主子:“有,有兩個年紀不大的孩子,奴婢給糊弄着放過了。如今人已經出府,不在府中了。”
徐宴緩緩地将名冊合起來。
修長的手指點在桌案上,一下一下地發出嘟嘟的聲響。這是徐宴的習慣,他思索的時候總是手指不經意地敲擊。他思索了片刻,又問道:“屍體還沉在長公主府的池底麼?”
“還在,”吳嬷嬷畢恭畢敬道,“長公主自那日殺了人,便命人連夜将池子給填了。去年年底之時,還特特找人移植了一片紅梅。紅梅種下去,大雪蓋下來,滿園飄香。如今半年過去,那片紅梅樹越長越好,長公主顯然已然忘了這片梅林底下埋了人。”
徐宴淡淡地笑了一聲,對此不置一詞。
晉淩雲的行事作風,他不做評價。上位者似旁人的命如蝼蟻,早在雙門鎮有人為了一套衣裳差點沒把蘇毓打死這事以後,徐宴就看透了這一點。
“勞煩嬷嬷費心,将所有涉及此事的人名冊,以及住址。能夠盡快查出來的,盡快給我。”盛成珏的這事兒不難查,難的是如何不牽連皇後将事情給捅出去。如今這長公主還是皇後的親生女,不管她所作所為是否是故意,皇後都逃脫不掉被盛家人憎恨的結果。
除非将晉淩雲的身份揭穿,但盛淩雲背後站着武德帝。況且,白皇後根本不願蘇毓卷進來,能瞞得住一時是一時:“若是有辦法拿住人,最好将這些人都藏起來。”
這事兒不難,吳嬷嬷本就是長公主府的管事,這事兒她過問不過是張張口的事兒。她此時看着眼前俊美無俦的年輕人,心裡翻江倒海,是與未央宮關嬷嬷一樣的激動。
吳嬷嬷與關嬷嬷一樣,早年是在未央宮伺候的。一左一右,都是白皇後從金陵帶上京城的。本就是她自幼一到長大的婢女,入宮以後便成了嬷嬷。這些年,她跟在晉淩雲身邊,是為了照看主子的女兒。比起關嬷嬷聽說長公主荒唐,她卻是親眼見證了長公主的荒唐。
驕奢淫逸,鋪張浪費,還整日裡折騰些神神鬼鬼煉仙丹的東西,最是難纏不過。這般也就算了,隻要不過火,左右皇家和盛家也供得起。但她偏偏就是不拿人當人看,明目張膽地強搶俊美男子入府。當着驸馬的面兒與面首談笑風生。别說驸馬那般傲氣的男子會受不了,就是她們看了都覺得傷風敗俗。
說起來,當初皇後就是怕晉淩雲沒規沒矩才特地将她給了晉淩雲。原想着替晉淩雲收拾爛攤子,順道管一管她的脾性。多年照看下來,吳嬷嬷卻沒法對這公主生出一絲愛屋及烏的憐愛。
這就是個自私自利的天生壞種,旁人的命都是蝼蟻。
原本以為好竹出歹筍,吳嬷嬷都麻木了。如今突然驚覺晉淩雲不是自家小主子,她鼻子就忍不住發酸。自家主子磊落了一輩子,果然不可能生出個這樣的壞胚子。
“姑爺放心,”知道這位是正主的夫婿,吳嬷嬷自然打起十二分的精神辦事,“奴婢省得。”
從天香樓出來,徐宴便折去了冀北候府。
半個月前,林清宇與友人京郊賽馬,不慎從馬背上摔下來。他那匹養了多年騎慣了的良駒踏月不知被人喂錯了什麼東西,橫沖直撞地發瘋。
林清宇那邊才沖進林子就被瘋馬甩下來,生生踩斷了他一條腿,踢斷了四根肋骨。
一身血的林清宇被擡回冀北候府,已經進氣少,出氣多。
老冀北候夫人李國夫人當場便吓得昏過去。索性林清宇這人命大,沒死。高燒燒了四五日,幽幽地又醒過來。一條腿被踩得骨頭都粉碎了,如今人躺在家中下不來榻。冀北候夫人如今宮也不進了,喪氣話也不說了。整日裡就在府中守着兒子,哭得跟天塌下來似的。
徐宴這段時日一直在忙,今日得了空,自然得過去看看。
他人到的時候,冀北候府還有别的訪客。不是旁人,是林清宇的摯友謝昊。因着林清宇的傷勢實在是太重,不便于被人打攪,李國夫人謝絕了諸多拜訪。這次徐宴能進來的,自然都是林清宇親口應允。
林清宇仰躺在床榻之上木愣愣地看着窗外,顯然,傷勢比徐宴想象得還要重。
“可查到是誰動的手?”謝昊臉色森冷,“是不是林邺峰搞的鬼?”
“不知,”林清宇盯着窗外樹枝上的一片葉子,“還在查。”
“不是他還能有誰?”謝昊啪地一巴掌拍在桌子上,霍地一下子站起身。林清宇這些年在京城雖有些花名兒,實際上卻不曾真正與誰交惡。若要說置人于死地的仇恨,除了林邺峰母子,還真沒有旁人。
“清宇,你還顧及你那沒良心的父親?你把他當父親,他可曾當你是他兒子?!”
林清宇不說話,扭過頭,不看人。
謝昊一口氣堵心口,無話可說。
“不是他的話,你還得罪誰了?”轉悠半天,謝昊滿屋子打轉,素來吊兒郎當的人伸着一隻手指着林清宇氣急敗壞地罵他婦人之仁:“還是那句話,養在你院子裡的馬,除了冀北候府的人能下手,我就不信外面人誰還能碰到你的馬!”
“宴哥兒,你怎麼說?”謝昊說不動林清宇,便将目光投向一旁的徐宴。
徐宴垂下眼簾,濃密的眼睫遮着眼眸,眸光幽幽的。頓了頓,他才淡淡地開口問道:“老冀北候是要帶如夫人一家上京了?”
一句話讓謝昊冷靜下來,盯着窗外樹葉的林清宇也轉過頭來。
“今年秋闱,府上大公子可是要下場?”
林清宇沉默了許久,牽了牽嘴角:“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