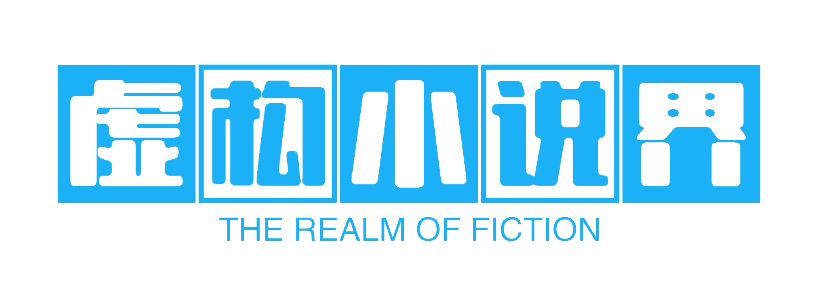又是一個豔陽天,太陽剛露出地平線,地上就開始蒸騰起來,樹葉兒呆愣愣的一絲不動,滿耳朵都是知了歇斯底裡的叫聲。
杜梅将天青色長衫洗了洗,晾在院子裡。吃了早飯,她帶上帷帽,扛着鐵鍬到田裡看稻子和旱谷長勢去了。
插秧的時候,杜鐘把田埂夯得實,這會兒田裡的水半淹着,一絲絲都漏不了,加之鴨糞施得勤,杜梅家的稻子明顯比旁人家的高大粗壯。
一根根葉片又寬又長,長得綠油油的,有一兩株性急的,已經抽出了半截穗子,更多的則驕傲地挺着葉鞘,像腆着肚子的将軍。
杜梅又轉去看河灘上的那塊棉花田,現下家裡姐妹們分了床,夏天不打緊,一張草席就行,可等入了秋,就得添置墊褥蓋被,可就指着這塊地裡的棉花收成了。
春澇的時候,杜鐘和杜樹在田裡開了很深的溝用來排水,如今倒派上了用場,杜樹在溝裡灌上水,地裡濕潤潤的,棉花杆子長得有半人高,成人手指粗,這會兒枝頭上已經打苞,正次第開花,引得蝴蝶蜜蜂團團飛。
田埂上的大豆已經結了豆莢,杜梅捏了捏,已經飽綻得可以吃了,她順手折了幾枝,準備帶回家,中午剝了炒來吃。
山林裡杜樹開荒種的地,雖開了溝,但因都是黃土,不存水,大豆長得又矮又小,才剛剛開花。玉米結了幾個穗子,胡子還是嫩黃的,明顯還沒成熟。
倒是南瓜長得好,枝枝蔓蔓爬了好大一片,有的還在開花,有的已經結了拳頭般大的瓜瘤子,杜梅将那一片南瓜的大葉子翻了翻,竟然還找出三兩個大的,隻是還是青綠色的,切絲放點辣椒炒了吃,最是美味。
玉米杆後面,種着一片香瓜和西瓜。香瓜結了好幾個,看樣子還得三兩天才能熟。西瓜倒是有幾個大的,隻是不知道該怎麼分辨熟不熟。杜梅挨個摸摸,想着等到搬家宴請的時候,摘了吃。
杜櫻正在河灘上放鴨,她戴着帷帽躲在鴨棚的陰涼處,這裡四周空曠,又緊挨着水面,所以并不十分悶熱。小母牛吃飽了,窩在鴨棚底下睡覺,尾巴來來回回搖着,驅趕蚊蠅。
村裡人為了不耽誤稻子孕穗的關鍵時刻,都在拼命車水澆灌,有的人家田埂做的不好,幾乎隔天就要車水,所以魚嘴口的水位下去得很快,鴨群越來越往水面深處去了。不過,鴨子在河灘上放養多時,早已老練,又有大白帶着,倒是不擔心會胡亂跑到射山湖裡去。
“櫻子,你回家去吧,我替你放會兒。”杜梅心疼大妹妹,這些天日曬風吹,臉上黑紅黑紅的。
“姐,沒事,你回去忙吧,家裡事雜,沒你在,可不行。”杜櫻笑着推她。
杜梅隻得回去。歇了晌,她就去請杜懷炳,請他搬家時來家裡吃飯。她家起屋造房,杜懷炳幫了不少忙,再說,他是杜家溝的族長和裡正,按規矩禮數都是要請的。
杜懷炳坐在屋裡抽煙,聽了杜梅說的話,點點頭算是答應了。
尹氏在旁問:“搬家可是大事,你都請了什麼人?”
杜梅也不隐瞞,把邀請的人一一說了。
“你不請你爺奶和大伯三叔家嗎?”尹氏試探着問。他們家的
龌蹉事,她也知道些,但她從大面上出發,還是覺得不妥。
“我不想請。”杜梅垂下腦袋,低喃道。說到他們,杜梅真是頭疼得很,實在不想和他們打交道。
“你們既然分家了,大伯三叔,你不想請就不請。”杜懷炳悶了兩口煙,咳了一聲說。
“老的還得要請請的,二房屋裡都是姑娘,将來還得出嫁。起屋造房這麼大的事,不請老人,實在不妥。外村人不知内情,隻當梅子她們不孝順,這種事最是會以訛傳訛,對她們将來說親不利。”尹氏看了眼杜懷炳,輕聲說。
“這樣吧,梅子,你爹呢,不在了。按說養老送終攤不到二房頭上。但分家的時候是有你爹那一份的,你好歹替他盡盡孝。
你若是在搬家這樣的大事上,都不請你爺奶,他們在村裡就實在太丢份了。你也知道,你阿爺最是好面子,他若高興了,與他的身體也有好處。”杜懷炳覺得尹氏說的有道理,他生怕杜梅不肯,遂苦口婆心勸道。
大順朝素以孝治天下,百姓也最講究孝道。杜梅知道杜世城夫婦是為她們家好,就算她有百個千個理由,也大不過一個孝字去。
“好的,我聽族長的,回去和我娘說。”杜梅隻得答應。
“真是個懂事的孩子。”尹氏愛憐地摸摸她的肩膀。
出了杜懷炳家,杜梅心裡百般不樂意,但也隻能忍着。她低頭走路,全沒看見不遠處的二愣子。
“嗳,梅子!”二愣子看見她,一邊高喊,一邊向她跑來。
現如今,他每日也有十幾文錢進項,日子過得滋潤起來,除了吃穿用度,他娘每月還能攢下些錢來。二愣子之前賣冰的工錢還存在葉青那裡,他每每思及,都覺得自己是個有錢人了,每日樂颠颠的。
“怎麼了?”杜梅還在想心事,聽見他叫,回過頭來,茫然地問。
“搬家這麼大事,你請大丫,為什麼不請我?”二愣子難得臉皮薄一回,盡顯委屈地說。
“我當什麼事,我不請你,你就不來啦。”杜梅嗤他,扭頭就走。
“這話說對了,你不請我,我也是要去的。不過,咱現在也是有臉面的人,蹭吃蹭喝多不好。”二愣子嬉皮笑臉跟在她身後唠叨。
“你哪來那麼多話,說這麼好聽,也沒見少蹭。到時直接來就是了,不過事前說好,旁人是客,你是來幫忙的。”杜梅有心逼他。
“對頭,咱一筆寫不出兩個杜字,我自然是半個主家。”二愣子的臉皮比城牆還要厚,給個杆就往上爬。
“話唠,哪裡的半個主家,是不是想找打!”杜梅心裡煩着呢,沒好氣地說。
“好好,這麼說定了,我走了。”二愣子看着杜梅似乎心情不好,也不敢和她插科打诨,擡腳溜走了。
“娘,族長讓我們那日也請阿爺和阿奶。”吃晚飯的時候,杜梅說道。
“為什麼請他們,他們害我們,害得還不夠慘嗎?”杜櫻聽了這話,第一個不幹了。
“就是,當初,她是怎麼罵娘的!”杜桃哼了一聲。
“太婆說,這關系到我們女孩兒的名聲。”杜梅悶聲說。她可以不顧這些虛的,可
她不能不替妹妹們想。
“還是請請吧,咱辦這麼大事都不請阿爺和阿奶,到時,外面又要亂傳,編排你爹的不是。”許氏咬了下筷子說。
“他們要是不來就好了。”杜桂撇了撇嘴說。
吃了晚飯,天色微暗,杜梅踟蹰到杜世城院門外,在門口掙紮糾結了半天,方才擡手叩門。
“來啦,誰啊?”魏氏趿拉着鞋子,從屋裡出來。
“阿奶,是我。”杜梅嗓子裡似有東西梗着,每說一句話,都艱難十分。
“你這會兒來做什麼?”魏氏将門開了條縫,驚疑地看着她。
“我有事和阿爺說。”杜世城畢竟是一家之主,杜梅就算請,請的也是杜世城。
“你阿爺好不容易睡下了,你想要錢的話,最好免開尊口!”魏氏嫌憎地說。
“我家四天後搬新房,我是來請阿爺過去坐坐的。”杜梅氣極,鄙夷地看看魏氏,就是不提請她。
“你這丫頭說話,也不一口氣說了,快進來。”魏氏變臉比翻書還快,這會兒,她開了門,滿臉堆笑,伸手就想拉杜梅。
杜梅輕巧地扭了一下,不着痕迹地躲開了她的手,閃身進了院子。
院子還是原來的樣子,這幾日杜梅見慣了自家的大院子,突然覺得自己打小長大的地方,原來這樣逼仄破舊。
屋裡尚沒有點燈,借着屋外的天光,杜梅隻看見杜世城一個輪廓,果然比半年前瘦削了很多,腮幫子都癟進去了,顯得顴骨老高。
“阿爺,四天後,我家裡搬新屋子,到時,請您過去坐坐。”杜梅也不坐,隻站在床前說。
“好啊……咳咳咳。”杜世城應了一聲,劇烈的咳嗽打斷了他想說的話。
“那我就回去了。”杜梅實在沒有什麼話與他們說,既然請過了,她就想離開。
“等一下。”杜世城緩了過來,喊住杜梅。
杜梅隻好折回來,隻見杜世城伸手在枕頭底下摸索,過了會兒,拿出一個舊帕子包的東西。
“我們也不知道你缺什麼,這有一百文,你看着買吧,算是我們的心意。”杜世城側身将帕子遞給杜梅。
“老頭子,你糊塗了,你這身子骨哪頓能少了藥,吃的都是錢啊。”魏氏一見杜世城要給杜梅錢,立時炸了鍋。
“阿爺,我不要,我家裡啥也不缺,你留着吃藥吧。”杜梅的頭嗡嗡作響,轉身就走,全沒想到她說的話,似乎哪裡有點不妥。
“當家的,我聽外頭傳,梅子掙了一大筆,她哪裡看得上你這點小錢。”魏氏将荷包緊了緊,又塞回枕頭下面。
“嗳。”杜世城複又躺平。他瞧着杜梅剛才如避蛇蠍的樣子,心裡實在不是滋味。這個孫女,他當初真的看走眼了?
杜梅一路小跑回家,她站在院門口,順了順氣,聽見家裡傳來妹妹們說笑的聲音,她的心裡才安定下來。
夜色慢慢籠上來,溫柔地将杜家溝擁入懷中,蟬歇了呱噪,隻有在這樣的深夜,才有涼風習習,并将遠處田裡的蛙鳴聲,一陣陣送來,做了令人昏昏欲睡的催眠曲。2k閱讀網